【在人間】不確定性與無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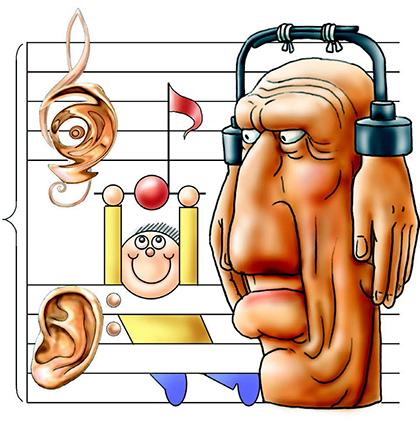
談蕭士塔高維奇們的作品,免不了要談廿世紀的樂壇新風即「無調性音樂」。「無調」是對「調性」而言。自巴洛克以降,調性音樂一直是歐洲音樂主流:曲子有和聲行進,不協和音得向協和音過渡,導音須轉到主音才能結束……但這些規矩是逐漸積累成形的,也不是沒有異數。二百多年前, 巴赫已利用連續轉調或半音暫時掛留,造成調性暫時不穩的懸宕效果,結句時回歸主音,讓人感到「一天光哂」般圓融;莫扎特更是此道高手,瓦格納進一步把這技巧發展到極至;到德布西則更獨樹一幟,充分利用三全音及全音階造成不穩定的和弦及音樂色澤效果,讓音樂「似霧又似花」……這些都可看作無調性音樂的前兆。到廿世紀初,此道蔚然成風,史特拉文斯基和理察史特勞斯令和絃間的鬆緊關係去到極限,調性最終被突破。於是便有奧地利人荀白克提出十二音列理論,即將十二個半音以同等的重要性排列,異於調性音樂強調主和絃、屬和絃,和下屬和絃,是最正式的無調性音樂理論。
有說無調性音樂曲高和寡,聽來不知所云。德布西們的樂譜都有調號,都有和絃,但用正統樂理常分析不來,其實已不用調性來寫作,卻很好聽。史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也涵蓋了有調號與無調號的世界,但有調號的不全都好聽,無調號的也不全都難懂。蕭士塔高維奇的作品則在有調性和無調性之間游移,不算難懂,長處是鮮活無比。無調性音樂其實很多也有頗迷人的旋律線,其出位不過是尋找正統調性規則以外的可能性。即使荀白克,他也寫調性音樂,其無調性作品也不如傳說般冷僻。竊以為,若能把瓦格納和馬勒等人的音樂聽得頭頭是道,聽荀白克便很易著迷。只要靜下心來仔細聽,就會發現個中趣味不在調性作品之下。
荀白克也是畫家,和「抽象畫」鼻祖康定斯基(俄人)、保羅克利(瑞士人)一起,屬於「藍騎士」集團,對現代設計學貢獻極大的「包浩斯」運動,這批人居功至偉。其實,當時風行至今的非具像繪畫和無調性音樂,不過是知識界高端的思想潮流的反照:當理性走到盡頭,我們直面的便是人類非理性的另一面。黑格爾們那套「歷史決定論」不過是當理性走到極端時,人類以為自家認知和意志萬能的錯覺。這心智誤區摧生了各色各樣的烏托邦美夢,理想主義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豈知黃雀在後。世事本來就有太多不確定性,人不是神,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是以昔人才有謂「近來始覺古人書, 信著全無是處」。在正能量主流大合唱中「跑調」的人,早期必是尊師重道者,吃虧多了,才知盡信書不如無書。若你理解這機樞,便可意會,調性音樂不錯好聽,但其圓融和完美有太多主觀上往好裡想的必然性,在真實世界裡,必然不過是無數偶然在條件剛好全在人為控制中的僥倖,要真正看透我們面對的世界與人生,無調性即不確定性,是否更貼近我們經歷了太多不堪後心緒中的「化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