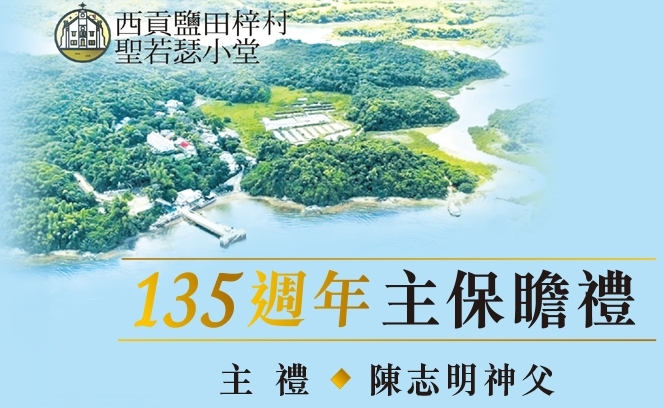【最藝術的時光】不要加霜
天文台說受到「拉尼娜現象」影響,本港的冬天可能會較寒冷。一提起冬天,教我頭痛,就是想法子如何對抗寒冷的入侵。其中不少得的「戰備」就是暖爐、暖包、暖毯、暖內衣、大羽絨、熱薑茶,更試過兩件羽絨「打孖」上,「瘦蜢蜢」的身形突然像隻大熊貓那般臃腫,畏寒懼冷真可怕。要是去寒冷的地方,真的不知怎樣面對。
惟有硬著頭皮抵抗嚴寒。有說全歐洲最高的山峰落在白朗峰(Mont Blanc),海拔為四千八百多米,它在法國與意大利邊界之間,山頭終年積雪。「Blanc」法文的意思就是白色,所以有人叫它做「白山」。雖然白朗峰屬於法國境地,可是由瑞士日內瓦出發只需七十五分鐘車程,而且交通方便得多。白朗峰山腳的地方非常美麗,這小村叫夏慕尼(Chamonix),聽說教宗若望保祿一世在生時曾踏上夏慕尼觀賞這座皚皚雪峰;而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更形容從夏慕尼眺望的白山是他所見過的最美的景色,真的很美嗎?
假如非親身經歷,不能相信有如此美如畫的景色。美如畫?的確,西方畫家也像中國畫家一樣以畫歌頌大自然的美感與律動,每幅畫都訴說了一段動人的心境與感嘆。就像俄羅斯著名的風景畫家艾薩克?列維坦(Isaac Levitan 1860-1900)被大自然的美景深深吸引著,在短短廿年裡畫了數千件作品,幾乎全部都是風景畫,一幅城市畫作沒描繪,只陶醉於大自然的美姿中。這幅《白朗峰》(Mountain Range. Mont Blanc)(見圖一),畫中遼闊翠綠的山巒蓋了一層層絲滑如紗的白雪,峰巒雄偉,形態萬千,令人讚嘆不已,好一幅景色畫,有種不捨離別山群的感覺。同一座山,經不同畫家在畫布上用顏料「攀登」,出來的是不一樣感受。美國畫家約翰•辛格•沙金(John Singer Sargent 1856-1925) 擅長肖像畫,他筆下的白山《Coming Down from Mont Blanc》(見圖二)沒有列維坦的白山那般蜿蜒崎曲,那般斑斕嶙峋。沙金的白山不像列維坦的那樣嚴寒酷冷,用大遍金黃色營造「雪中送炭」的溫暖感覺。
不是只說說看,而是真的親睹白山面目的真風采,今年暑假終於有機會登陸「死亡之峰」。由於天氣常常變壞,容易出現雪崩,「死亡之峰」因而得名。怕冷的我當然不會徒步攀上山頭,只能搭乘纜車上山至三千八百多米的白朗峰觀景台。纜車窗外的風景已「化了白妝」,圍繞著盡是終年不溶化的冰雪及冰河。甫出纜車門,走出觀景台,橫風橫雪狠狠拍打我的面頰,嘩!僵凍入骨,真不好受。
不好受?肉體上任由風雪摧殘,是難受的,只要做足禦寒措施,也會迎刃而解。可是精神上受盡「人間的霜雪」所折磨,更不好受。受對方冷言冷語的辱罵,盡失尊嚴;冷眼旁觀者不伸援助之手,任由痛苦的人受苦;社會上的冷酷無情,使眾多百姓得不到關懷及平等對待。看盡世間冷漠,我們更不應做「冷血人」在雪上加霜,應該雪中送炭,點燃愛火。耶穌來世時沒有「加霜」,卻比「送炭」更要命的,為愛我們白白「送命」,流盡他的熱血。「熱血耶穌兵」抑或「冷血耶穌冰」?你願做這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