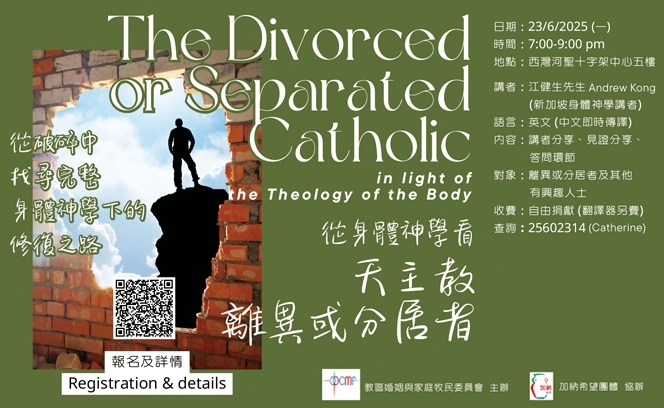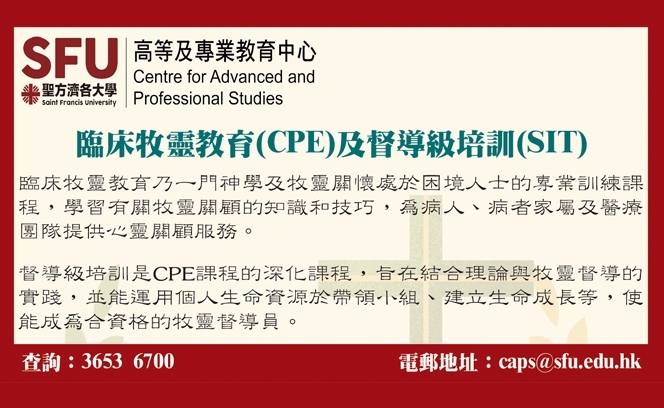悼念區海晏修士(上)
我在一九六O年下學期考入九龍鄧鏡波學校,插班就讀「工業中學預備班」(p. form 1),其實是當年的小學大部分用中文授課,如果直接升讀全英文的工業中學,學生會很難理解老師的授課,所以九鄧開辦了這預備班,以全英語授課,讓學生在升工業中一時能夠跟得上課程。我第一天上課,早上便是「投影幾何」,是機械繪圖的基本課程,要動用T 尺、角尺、鉛筆及畫紙等繪圖工具,當日第一課的老師便是區修士,雖然我初來步到,但是已知道這位老師非同小可,全班同學在老師進班房時已正襟危坐,鴉雀無聲。這樣的威勢,我在以前的學校從無得見。
區修士進班房之後,沿著每行的座位通道巡視一面,來到我座位前面,一手抓起我?面的鉛筆,從中折斷,大力拋出室外,又將枱面的橡皮擦膠拿走掉到廢紙箱,他不發一言,但全班同學都感害怕,我身為一個新來的學生,自然無所適從,不知有甚麼得罪了他,也不知自己犯了甚麼錯失。當日上堂自然專心致志,留心聽講,不敢怠慢。
下課後我仍不敢去問區修士我犯了甚麼錯,鄰座的同學好心告訴我,因為我是新來的插班生,不知道區修士的要求非常嚴格,他折斷我的鉛筆,相信是因為我的鉛筆刨得不夠尖,他丟掉我的擦膠,是他不容許繪圖有擦拭修改,同學警告我說,最好帶備小抹布,隨時抹乾淨所有繪圖工具,他若見到畫紙上任何污痕,他二話不說便會撕掉你的功課,若果測驗或考試,儘管繪圖正確,他只要見到污跡,或線條不夠尖銳均勻,肯定也是一個大 X 給你零分。
我當年的感受是這個老師矯枉過正,不近人情,不可親近,而且確實有一年時間,看到他迎面而來,我會轉頭走避。在學校日子久了,才發覺全校學生對他又敬又怕。他是一位輔理修士,英文尊稱為「brother」,是天主教修會中神父「father」以外的職級,一般輔理修士都學有專長,區修士的專長便是印刷、攝影、音樂和美術,他曾往意大利受訓多年,學習印刷及攝影(估計應該是製版,因為攝影和製版英文同是 camera,事實上無論攝影或製版都是他的專長),他可以說流利的意大利語,而音樂是他的興趣,他很有天分,可以玩所有的樂器,他在九鄧擔任樂團指揮,在他指揮期間,九鄧樂隊榮獲香港音樂節全港校際冠軍。他也在教堂司琴,彈奏手風琴更是出神入化。他又精於繪畫,我在寄宿期間,一年颱風溫黛襲港,沙田水浸死了許多人,連沙田聖堂也淹沒了,當年聖堂一面牆壁的大壁畫,是區修士多年前的作品,水浸後壁畫有小部份損毀,他帶同畫具和我去修補,那是我唯一一次為他修補作品,他有這麼多傑出學生,卻只叫我去,而又信任我可以修補,至今我仍感榮幸。
我因家庭問題放棄升讀工業中學,九鄧有三個學部,最難考入便是英文教學的工業中學部,當年與香港仔工業學校齊名;第二便是文法中學的中文中學部;第三是有技能訓練印刷和洋服的職業中學部。第一及第二個學部的學費及雜費比職業部高四倍,我家人為了節省開支,要我轉讀職業部,我曾跟老朋友說,若我不是父母早死,家人願意繼續支持我升讀工業中學,我肯定會是一個出色的工程師。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