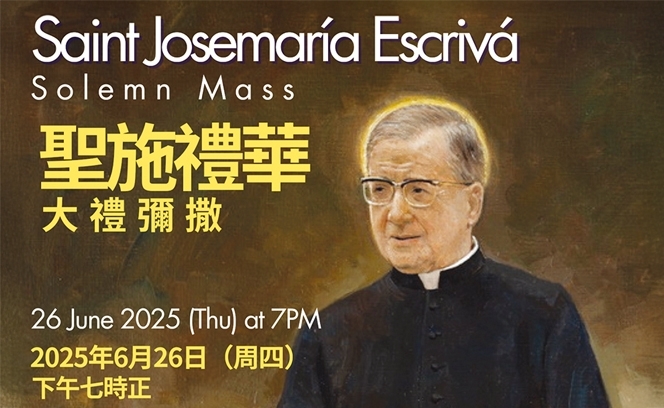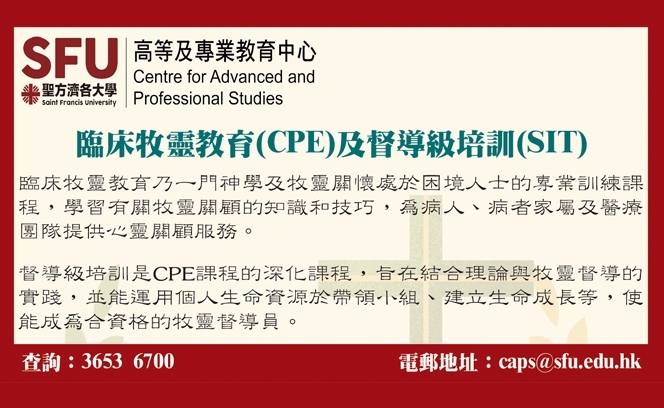修院跪櫈不見了!聖召何處來?(下)
記得早年初入西貢聖神修院時,有一天清晨五點左右,天還很黑,我起床經過聖堂時,看到院長江志堅神父,一個人跪在聖堂中祈禱。他沒有開電燈,而是點著一盞油燈,放在跪櫈的扶手上,全神地拿著大日課經書祈禱。這件事雖然已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但對我來說,仍然記憶猶新,江神父的信德和聖德,他的虔誠和刻苦精神,對我和當年在修院的修生來說,都有很深的感召力。
江志堅神父後來在九龍玫瑰堂服務,他的謙虛和聖德,一直受人敬仰。退休後在上水聖若瑟安老院,長期對聖體聖事的崇敬與熱愛。據說他也是在聖堂中朝拜聖體時安眠主懷,回歸天鄉,享年一百零一歲。
還記得江神父做院長時,每天早上晚上都是與我們跪著念經祈禱,早晚課和默想都是一起做,朝拜聖體和聖體降福都是跪著做,因此每個人的膝蓋上都跪了一個印記,下午運動打球時,大家都顯出了膝蓋印,我們開玩笑說:「這是『升天印』!」有時更拿來比比,看誰的「升天印」更深!在修院的生活中,許多不足為樂的事,大家都會覺得很快樂,也不知為甚麼,在團體生活中,許多時大家會為一點小事,竟然會引起哄堂大笑。而這種從心裡發出來的歡樂,是無法在世俗社會中找到的。因此,真正的修院生活,雖然在外面世俗上看起來,是那麼單調,那麼清淡,那麼簡樸,但是竟然會那麼開心快樂。從這一點上,使我想起了大嶼山的苦修院為甚麼會稱為神樂院了!我肯定地說,真正有聖召的人,一定會感受到修院的樂趣,連長跪祈禱也是一種神樂的根源。
說到這裡,我能再說甚麼呢?修院的院長神師們,可能也受到世俗化的潮流影響,把禮儀改革到不需要跪櫈了,也可能他們認為念經祈禱、參與彌撒,並不需要跪下了,只要從心裡朝拜天主就夠了。其實不然,我從二OO五年至二O一O年在多倫多總教區的華人堂區服務。多倫多總教區對聖堂禮儀的規矩很嚴。在彌撒開始時,神父與輔祭入堂時,在到祭台前先向祭台鞠躬,後向旁邊的聖體櫃單膝下跪,然後才上祭台,每個教友都在入堂時同樣先向祭台鞠躬,後向聖體櫃單膝下跪,彌撒進行中,從聖、聖、聖開始跪下,一直到念或唱天主經時才起立,我感覺這樣的禮儀,才相稱聖堂及對聖體聖事的尊重!
在多倫多的中華殉道聖人堂,令我很感動的是教友對聖體聖事的熱心和崇敬。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有一個小時的明供聖體,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特敬耶穌聖心,從早上彌撒後就有明供聖體,一直到星期六早上彌撒前結束。而在首星期五晚上除了彌撒外,另有一個多小時的集體祈禱唱經,有特別為聖召祈禱的禱文,有請神父或修士、修女教友分享聖召或朝聖的心得。教友能夠保持二十四小時輪流朝拜聖體,尤其是在寒冬的晚上,外面大雪紛飛,氣溫在零下十多度,但教友對朝拜聖體的熱情,好像已融化了冰雪一樣,沒有放在心上。
我們香港教區到現在還很難找到一個這麼熱心恭敬耶穌聖體的堂區,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我也知道黃靜儀修女一直在推動對朝拜聖體的敬禮,還有九龍鄧鏡波學校的聖母進教之佑聖堂,也在推動朝拜聖體的神工,但是仍然沒有得到教友的熱烈支持,實在也是一種遺憾。
最後我想引用一段聖經來結束本文,斐理伯書中這麼說:「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斐二8﹣11)我絕對相信,如果全香港教區、堂區發起以熱心敬禮耶穌聖心和明供聖體,為聖召祈禱,而修院也能改善聖堂的基本設備——跪櫈的話,鼓勵教友和修生朝拜聖體,熱心誦念聖召祈禱經文,天主一定會俯聽我們的祈禱,打發更多的青年使他們得到聖召,追隨聖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