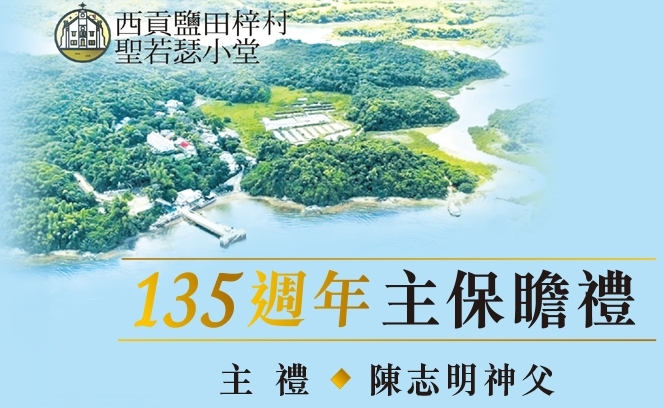【在人間】聽樂偶感
這幾天腦際總有些音符在浮沉,是巴赫《哥德堡變奏曲》裡開頭幾句,打從在HBO頻道上重看了《沉默的羔羊》的續篇《漢尼拔》,便揮之不去。電影裡,安東尼霍普金斯飾演的那位智商超標的吃人魔邊撫弄鋼琴邊沉思時,彈的便是那麼幾句。記得《沉默的羔羊》也拿過此曲做配樂,原著小說亦云此君極愛此曲。恬靜優雅的巴赫樂句反襯著變態奇才的兇殘,乍看矛盾,但魔鬼本是驕傲天使,人的智慧過了頭便成魔道,在現實中我們見識得還少嗎?
巴赫此曲寫於晚年,那時他的視力已每況日下,幾年後便在失明的黑暗中去世。此曲據說是他寫給學生哥德堡彈奏,好讓某伯爵失眠時舒緩心情的,但經考證是後人附會,何況此曲有些變奏頗沉重,全曲也不太好懂,並非一服輕鬆的催眠藥。而首尾呼應的那首詠嘆調,原本出自巴赫在中年續弦時寫給小嬌妻練琴用的那本著名的《安娜瑪德蓮娜曲集》第二卷,易懂而柔情,但中間那三十個變奏常異峰突起,氣象萬千。沒有人知道巴赫為甚麼要寫這變奏曲,但可以肯定,這本曲集和他那些以嚴謹和艱深著稱的《十二平均律曲集》或《賦格的藝術》等作品一樣,作者透過嚴格的樂理邏輯推演,看看由一闕簡單的如歌調子,如何能變奏出一個壯觀的七彩繽紛的音樂世界。你不妨把巴赫這類作品看作他在音符世界裡構建出來的小宇宙,那是他心中的大宇宙本相的微縮。當然,他憑借的是音符而非文字。
以前人們都把巴赫這曲看作充滿學究氣的樂理推敲,敬而遠之。如今凡是巴赫的唱片專集都會收錄此曲,得多虧五十年代初加拿大鋼琴怪傑顧爾德出了一張見解獨特的唱片,人們聽罷才驚嘆,巴赫此曲簡直是鬼斧神工,以致後來有許多演奏家才樂於在此曲中探索其深意,但行文造句多少都受顧爾德啟發。樂迷只道顧氏手中的巴赫是絕活,是純正的巴赫,殊不知他原充滿浪漫派傳人意味,反叛得很,最服膺的是勛伯格的十二音列作品。十二音列樂理是二十世紀音樂新潮的基石,用它去解讀古老的巴赫作品乍看不可思議,但藝術的至境,新與舊本來就相通。我猜巴赫若泉下有知,也會挺有興味地聽巴爾托克們的新作吧?
聽巴赫這變奏曲,常令人覺得韻味無窮,但即使每句都聽得搖頭晃腦,卻只覺神妙和親切,卻不知從何說起。我猜,是由於它確乎說了些甚麼,卻又充滿不確定性。其實,人生也好,樂理也好,宇宙觀也好,若真到家,都在確定與不確定間徘徊。昔人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說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間。道在雲深處,也在經書裡,更在穿衣吃飯間。它一說便死,一說便俗。俗世常把一切既懂的看死說死,但真理就在對立的兩極之間,有與無之間,確定與不確定之間。有心人是可以在巴赫的音樂裡參透世界奧秘的,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