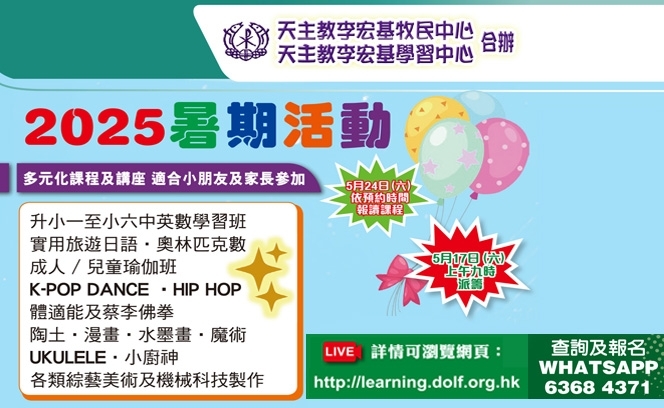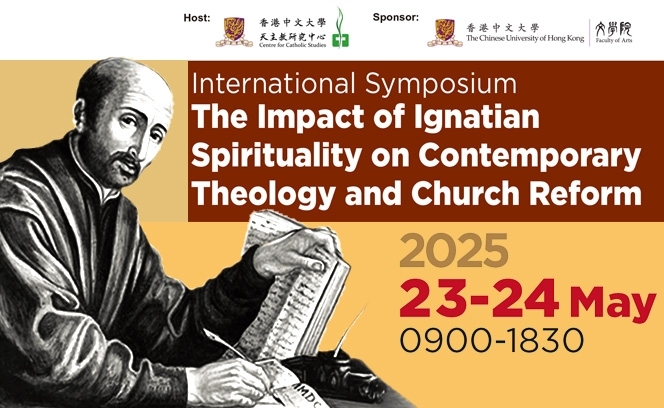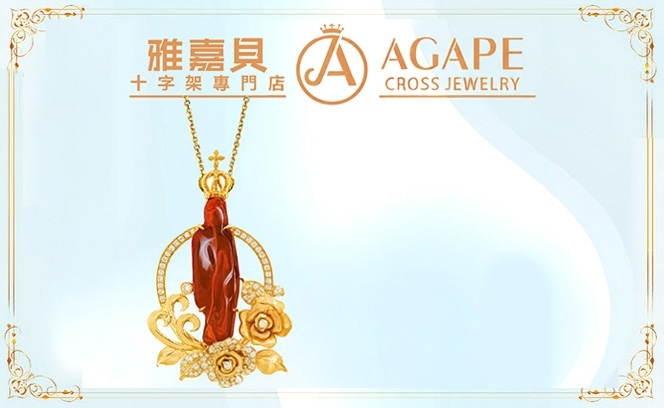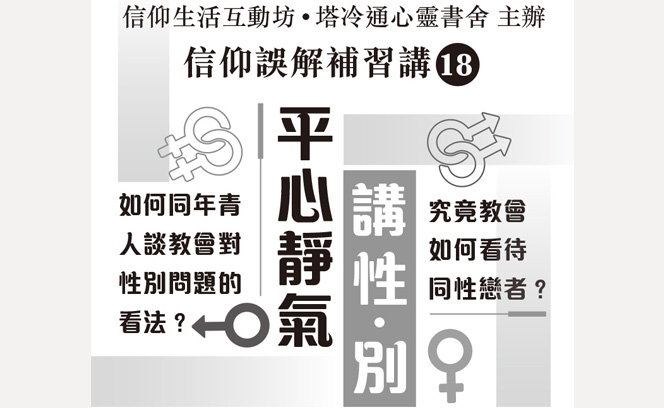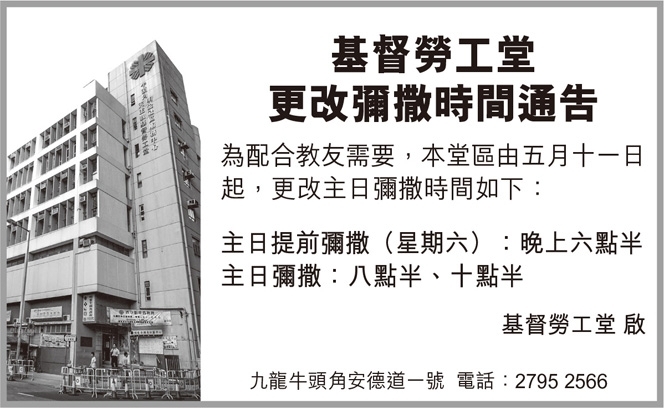【在人間】語 感
許多人以為寫好散文是寫好詩的基礎。但人類最初碰上事情,先是止不住驚呼或嘆息,用音調變化發洩情緒,慢慢才產生語言。因此,歌謠比純敘事的話語早,吟詠也定比散文要早。音韻和節奏既比意符萌發早,我們為文時,文字也必先以語音在作者腦裡醞釀,讀者亦必先感應作者的聲律。是以若寫作時留意聲韻和節奏,發揮語感優勢,文字定多幾分魅力。
古人很懂這一套, 孔子教兒子「不學詩,無以言」。西方人最早的著作是《荷馬史詩》,可用詩琴伴著吟唱,我們的古代文人幾乎無人不工詩詞歌賦。詩詞要押韻,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為甚麼?是因為單句若提問,雙句如作答,和音樂一樣,有問有答,詩才有氣脈和圓融。而句與句之間,一句中的詞序之間,平仄都得考究,失調便叫「失對」或「失粘」,宋以後讀書人都懂箇中規矩,若出毛病便很羞家。但早期的詩,連有些名句也未必符合後世規範,正如巴赫的樂句不一定都符合對位法定則一樣,我們也不必拘泥和望而生畏。昔人的好句讀多了,音韻節奏便可在我們心底裡潛移默化。以粵語為母語學中文的人, 因為粵語音韻豐富,貼近古音,天生就有容易掌握古詩詞音韻的優勢,若下筆時充分體會文字的節奏和韻率,信手寫來,未成曲調先有情,筆下的白話文較易多添韻味,亦很自然。
中文成語多為四字句,而最早的詩歌和散文,如《詩經》或《尚書》,也是四字句居多。舊時學童開蒙時念的《千字文》, 通篇也是四字句,用千字便把我們周遭的世界說得面面俱到: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星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這些四字句為甚麼那樣簡潔有力?是因為裡面全是實字。自古我們要把意思說清,不必訴諸複雜的句子結構,只要有機地把實字疊合在一起,便可言簡意賅地讓讀者一目了然,心領神會。自始,四字句便成了文言文一脈相傳的最重要句式,直到如今在白話文裡仍是這樣。
古人認為,實字是文章的骨骼。若我們讀慣這句式,便不須把句子寫得又長又臭,試試像古人那樣,先把實字疊合,若通順便可。但有時適當加上了虛字,便更生動傳神。但怎麼加虛字才是上策?古人不會寫一部語法大全,而讓小孩一早就背熟《三字經》。和《千字文》相比,它是另一文體:「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每句中間的都是虛字。有了它,句子便能起承轉合,意思和調門便活了起來。《千字文》沉實厚重,《三字經》奇詭多變。兩篇東西其實相輔相成。若這些句子朗朗上口,自能從中體會到實字和虛字的用法,讓它靈動起來,筆下的字句便容易節奏明朗,簡潔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