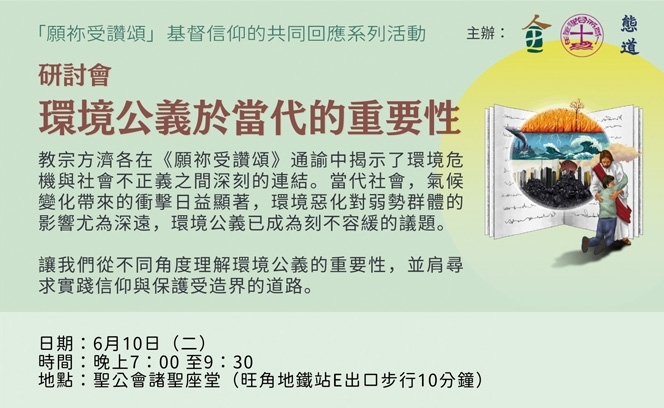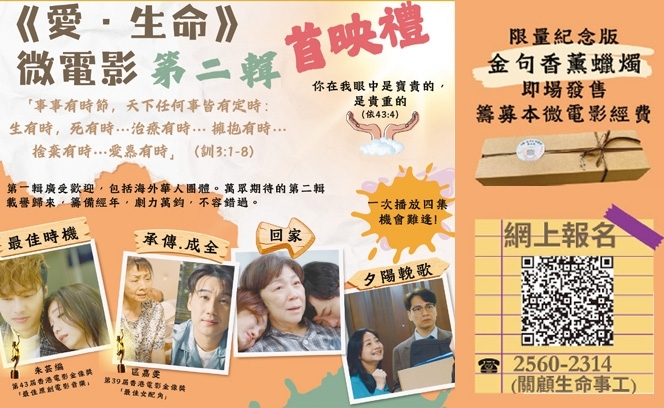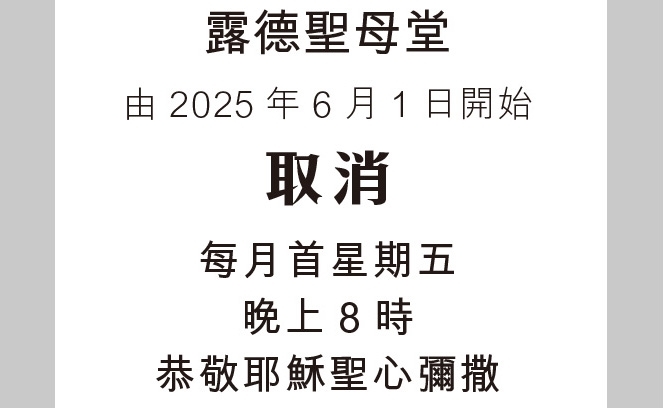【在人間】造化與心源
唐時有位名畫家叫張璪, 擅畫長松大壑, 與王維同時而更負盛名。有人問他作畫之道,答曰「外師造化,中發心源」,這八字真言後來成了畫道座右銘。坊間多把「造化」解作「大自然」, 但這概念在西方亦只見於啟蒙時代之後,張冠李戴,昔人豈不都成了盧梭主義者?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自古只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造化」一詞出自莊子,本指造物主,只不過「子不語怪力亂神」,古人不會隨便給本就無名, 也無以名之的屬神位格命名罷了。弄清這分別很重要,否則,董其昌就不會說「畫家以天地為師,其次以山川為師,其次以古人為師。」在昔人看來,法師「大自然」者只屬次等,高手「師」的是「天地」而不是現世裡的山水樹石。古人把能看能碰觸的存在稱為「物」,與「心」相對。宋以後,三教相互滲透,禪宗和理學都講心性,王維以禪入詩入畫,董其昌的畫室就叫「畫禪堂」,都強調心性而力求擺脫「物」的覊絆,誰會提倡以「物」為師?北宋的山水大師范寬就說過:「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說的是師古不如師物,師物不如師心,「外師造化」由是便轉回「中發心源」。「心源」本佛家語,亦即真如。心為萬有之根源,故稱心源。簡單地說,即認為人原都有個清淨微妙玲瓏的本原世界,即人的本覺;被世俗染污,才墮入迷霧;而妙悟就是恢復靈魂的覺性。好詩好書好畫,只會出自看破紅塵的潔淨空靈的心境,由心源導出。元稹詩曰:「我去淅陽山, 深山看真物。」禪宗公案也有說: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辛詞有道:「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要看到山山水水背後的真章,先要看你是何許人也。是以宋代畫論也強調:「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這「人品」不是簡單的道德品格,而是大覺大悟後人的品味,覺性和根性。
黃公望本姓陸,過繼與一黃姓老翁,翁曰「黃公望子久矣」,於是取名公望字子久。他少有才名,精通三教九流,口若懸河,求教者絡繹不絕,做過小官,曾因冤獄被囚,出獄後孑然一身,五十多歲才學畫,一學便精到,晚年隱居富春山,作此圖時年近八旬,題贈給朋友無用師。據說他「愛狂飲,日沽一罌,臥於石梁,面山飲,飲畢投罌於水而去」,「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不測其所為。又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詫而不顧。」這物我兩忘的意態可謂「外師造化,中發心源」的活畫。然則,他在個中又頓悟到甚麼?這頓悟又怎麼轉化為畫呢?(「到富春江去讀黃公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