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捉錯用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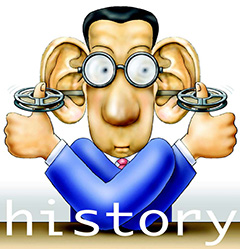
近百年談馬克思的書汗牛充棟,但把他按自家需要大書特書者眾,柏林圍場一倒,他又如明日黃花,問津者杳。國人認識的馬克思乃從蘇俄移植,難免染上斯太林色彩,後來馬恩全集的漢譯本雖洋洋五十五卷出齊,即使在最火紅的年頭,號稱他信徒者, 卻大多連半隻字都沒讀過,但這不妨礙人人堅信自家信奉的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可惜馬克思在生時就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思想一旦成為「主義」,便給定了型,且極可能是把某個片面定型,誇張到另一去處。馬克思的書充滿矛盾,他定沒想到,他的大作留下來的「手尾」,在廿世紀竟變成他徒子徒孫們你死我活爭拗的理據,也更沒料到,他的片言隻語會變成真理霸主們的盔甲。據說他女兒曾請他用最簡單的話去形容自己,答曰「懷疑一切」,這「一切」也該包括他自己說過寫過的吧?馬克思學說是十八世紀理性主義走到盡頭的產物,國人公然把它變成一種「信仰」,他不是思想家,說的便不是他一再強調的科學,而是神諭。把他捧上神壇, 看似尊重,其實非驢非馬。這老人家九泉有知,作何感想?
一個人的立論和觀點可由稚嫩到成熟,可推翻舊說而改宗,但初衷卻會始終如一。讀馬克思的書,不難發現,有些最基本的取態,在其早年直到他寫《資本論》的深思熟慮時期, 一直沒變。那正是西方文化最根深蒂固的追尋,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啟蒙主義、德國浪漫主義都一脈相承。而構成馬克思學說中對共產主義和未來社會人該怎樣生存的想像,若尋根究柢,都來自這脈胳而一以貫之。說來笑話,那恰恰是在某些奉他為宗師的去處,曾給當局極力詆毀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有許多年,「言必稱希臘」仿如罪惡,但馬克思初出茅蘆的博士論文就是《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可見浸潤極深。都說馬克思的思想淵源一是德國古典哲學,二是英國古典國民經濟學,三是法國社會主義,其實他最深的思想淵藪是古希臘哲學。寫《極權主義的起源》和《平庸之惡》的漢娜.阿倫特有本書叫《過去與未來之間》,首篇是對馬克思觀念形成的研究。她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不是烏托邦,而是對同一個雅典城邦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再現。而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說,雅典城邦是他們經驗的模型,並因此是我們傳統建立的基礎。」她真夠眼力。
離開昔人所在的社會文化氛圍甚至語境去讀他們的書,未免暴殄天物。讀馬克思,會發現他和黑格爾在對話,和李嘉圖和亞當斯密在對話,和盧梭及羅伯斯庇爾們在對話,甚至和蘇格拉底及其之前的哲人在對話……他使用的概念和思維範式,其中不少承接著曾被他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先行宗師。他不錯是個反叛者, 但反叛的深層,卻流淌著宗師們最珍惜的東西。只看到馬克思的「破」,卻看不到他的「立」,即他自始至終沒有移動過的立腳點, 對馬克思捉錯用神,錯不在昔人,而在太急功近利的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