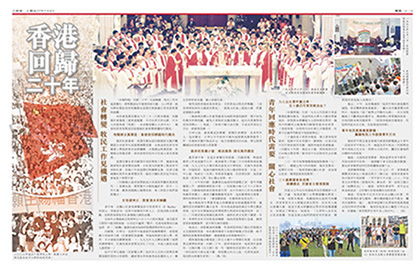香港回歸二十年
社會轉變 牧民工作見機遇
(本報特稿)回歸二十年,社會轉變,牧民工作亦起著變化。將軍澳是近年發展的新市鎮,人口眾多,區內聖安德肋堂的牧職修女莫慧宜便談論目前堂區牧養的挑戰。
母佑會莫慧宜修女六月二十二日對本報說,回歸後社會環境「愈來愈艱難,令市民看不到出路,不少人也愈來愈『現實』,未必願意關心人及付出」,她指培育者須幫助信徒透過社會訓導辨識時代徵兆。
牧職修女莫慧宜:紮根信仰辨識時代徵兆
談到社會發展,莫慧宜修女指回歸後新市鎮不斷擴張令堂區等社區服務團體受壓,未來或須安排在明愛專上學院新校舍加開彌撒,才能滿足牧養需要;而剛過去的復活節,該堂區便有近四百位成人及兒童領洗。
莫慧宜修女於回歸那年仍於學校工作,她說本地教會對社會訓導的演繹,正好套用到教學上幫助青年面對社會,而她十年前起擔任牧職修女後,也著力透過關社組作社會訓導培育。她坦言關社組在近年的社會氣氛下經營不易。
「回歸後正是堂區開始成立堂家組和關社組的時代。」莫修女說,將軍澳不少教徒處於青、壯年,工作忙碌,雖然仍能熱心服務堂區,惟工時長令他們面對壓力。
甘浩望神父:對香港未來樂觀
多年來一直關心社會基層權益的甘浩望神父(F. Mella) 則指出,香港當局一直排斥弱勢的外來人士,但他仍對未來樂觀,並期望基督徒在社會發揚天國的表徵。
宗座外方傳教會甘浩望神父六月十六日對本報說,當局從昔日對待中港分隔家庭,以至近年處理「雙非」兒童的政策均欠缺包容,而「『港獨』論調也是因為政府這種政策而衍生出來」。
回歸後,甘神父一直陪伴中港家庭爭取團聚權利,更曾跟陳日君助理主教(其後擢陞為樞機)等協助無證兒童入學;然而,不少家庭仍團聚無期:「一九九九年人大釋法剝奪了他們的團聚權利,往後的政府政策也分化了市民,本地人認為內地人搶資源。」
近年甘神父透過「居留權大學」這所非正式的小型學堂舉辦流動性質的小型課程,讓新移民和來港尋求庇護的人士、難民等學習新知識,融入香港社會。
被問及對香港前景的看法,甘浩望表示對世界樂觀,「因為基督徒相信天國就在附近」,要致力在地上建設天國,抓緊並發揚其表徵。
「教會與其擔心社會問題及內地對香港的操控,倒不如先抗衡世俗價值觀,避免只著眼於金錢及權力,這比共產黨管治更值得擔心。」他說:「如果中國只求自強,不求文明及民主自由,就會很危險。」
甘神父說,教會應成為橋樑,推動社會團結,也善待外人,包括難民。甘神父早年曾到中國內地服務及參與教育工作,但後來有數年無法回去,他月前獲准再回內地,神父期望繼續為有需要的弱小者服務。
退休校長楊少雄:教改過急 師生無所適從
教育多年來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回歸前後,特區的教育工作更成燙手山芋。從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年的榮休校長楊少雄一九九七年九月履任聖若瑟英文中學校長,至兩年多前榮休。回憶從前,他說回歸時抱著正面心態面對前景;可是二十年已過,他會以「失望」形容當前處境。但因著信仰,他仍會抱著「希望在人間」的心態去面對一切。
「二十年前回歸,脫離殖民地政府的感覺正面,當年周邊樓價上升,感覺經濟前景不俗。」信徒楊少雄六月十六日對本報說,回歸後他對政府愈來愈失望,其中在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教育事務上,政府不斷推動教育改革,包括教學語言政策、學科和學制等方面,「發展雖創新,但教師卻身受其苦」。
楊少雄提到中學教育最大的轉變是加設通識教育科,通識科旨在訓練學生獨立思考,但內容或會過度廣泛令學生難於掌握,近年又有輿論指此科導致學生對政府有過多批評,而二○一二年政府欲加開國民教育科,最終在多方反對下擱置。另外,各學科亦有不同程度的轉變,他批評政策推行急進,教師須重新適應教學,更令師生無所適從。
他表示,面對教改的挑戰,作為校長的他只能以有限能力去支援教師需要,如在教師發展日加強紓緩壓力等活動、給予教師更多參與校政機會、透過團隊支持與教師同行。
榮休後的楊少雄現於三所天主教中小學擔任校董,以其專業支援學校需要。回歸二十年,展望香港前景,他希望社會終有一天能回應《天主經》的一句「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相信政府不會永遠不變,即使難以在自己這一代看到成果, 我仍對未來懷有希望」。(鄧╱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年回應時代需要 關心社會
九七出生青年黃日希: 五十歲仍可享宗教自由?
(本報特稿)生於一九九七年的黃日希是聖德肋撒堂教友,也是科技大學天主教同學會成員。即使從未經歷過九七前的殖民管治,她仍不時聽到父親慨嘆回歸後香港再沒希望, 「爸爸常說,以前的自由社會已不復從前,社會不公義等問題更令他想過移民」。
二十歲的黃日希對本報說,港人事事批評政府,這跟中共未有履行一國兩制,以及市民不信任特區政府有關。她對香港前景感憂慮, 「回歸五十年時,我也五十歲,那時我仍可以自由進出聖堂嗎?會否因中共反對而失去宗教自由?」
二○一四年雨傘運動後她開始參與「七一遊行」,剛過去的六四祈禱會,她首次參加, 更擔任司琴,「我希望藉此關心社會,並表達出追求一個理想政府的期望」。
二十歲慕道者吳佰乘:修讀歷史 求證昔日香港發展
同是九七年出生的慕道者吳佰乘剛於六月滿二十歲,他現於樹仁大學修讀歷史學系二年級。他對本報說,他聽過殖民地時代的歷史,而當看到不少人都懷念殖民管治,甚至有人提出港獨言論,這更令從未經歷殖民管治的他修讀歷史,好能更了解過去。他認為,「大部份人並非真正追求港獨,而是反映出他們對政府有所要求,冀望政府重視港人的聲音」。
過去二十年,吳佰乘感到「這些年來社會流動性減低、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歷史並非職業導向的科目,他認為「除了教學之外難有出路」,坦言面對職場上不斷增加的競爭力,確會擔心畢業後的前景, 但他仍對未來充滿希望,「即使香港政治環境差,但這裡仍是自由之地,也是我成長的根」。
青年牧民委員會莫靜儀:冀藉牧民工作啟發青年方向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執行秘書莫靜儀過去十多年一直從事青年牧民工作。她認為青年牧民工作能幫助青年尋找人生方向,明辨天主的召叫,繼而引發他們回應時代的需要。
她說,大型的培育聚會,例如是普世青年節等, 有助加深青年信仰:一起經驗十多天的宗教活動後, 參加者多渴望這份信仰經歷能延續下去。
莫靜儀舉例說,二○○三年七月一日,多個教會團體及堂區走上街頭反對廿三條立法,當時青委會有份召集青年當糾察,「青年當中不少是二○○二年加拿大世青節的『留港世青』參加者,那一屆的主題正是『地鹽世光』」。她說,面對社會事件,青年走出來表達訴求,正好履行信徒地鹽世光的使命。
她說,信徒各可以用不同方式去關心社會,而「每當參與社會行動時,總有機會遇見青年教友,繼而自發聚在一起」。她形容這種百花齊放的現象與過去的信仰培育相關, 她相信這是良心驅使下而走出來,亦讓她「看到聖神在青年身上的召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