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拍手笑沙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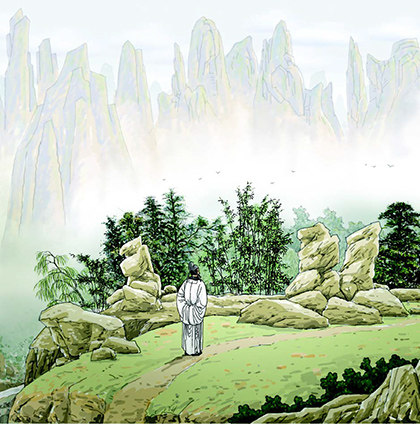
人面對著這光怪陸離的世界,不免戚戚。上下求索去讀書,在已故先賢的故紙堆裡尋答案,換來的常是更大的戚戚。積鬱日多,有時午夜夢迴,或白日裡獨個兒發獃,思緒便會在心頭纏繞,於是讀過的人和事,仿佛化作百味紛陳正反交錯的一大渾沌,世道和自己仿佛便都包容在這渾沌裡。人若還有幾分熱血和不岔,按孟子的說法,便是有股「浩然之氣」;若看破一切紛爭想超脫出來,便成了「士氣」,倪雲林說「余之畫蓋寫胸中之逸氣耳」,指的便是這氣場。兩者取態雖一熱一冷,其實相通,後者不過把鼓其餘勇的蠻牛姿態改成「道不行則浮槎於海」罷了。兩種傾向在無可奈何的渾沌裡不住整合重組, 便構成了古今士人的道統,與西方文化「知識分子的良心」是同一碼事。竊以為,人若心中有這渾沌及氣場,窘惑便容易明白,面對這陸離世道該如之何,也篤定許多。我不知道這有點浩翰的渾沌之境該何以名之?但既然思想史、藝術史甚至正史記載的,其實都不過是人在不斷試錯,試圖找出讓自家能「心息」的所在,把昔人的心理能量積聚作最大公約性貭的猜測,叫「心靈史」,也許還合適吧?古希臘人的壁畫把死者的靈魂畫成在茫茫大海裡往前游的人,游向哪裡?畫者沒說,但何必說呢? 每個靈魂都有自家的彼岸,游不到那兒是不死心的。我們和昔人一樣,都只不過是在這茫茫滄海裡浮沉的孤獨個體,作派不同,不過因不同的緣由作了不同取捨,但為堯成紂最後都是匆匆過客,最偉岸的也不過留下點滴的生命餘韻供後人憑吊。
佛家把這心靈之海叫無邊苦海,玫瑰經說人生是涕泣之谷。其之所以苦和涕泣多於歡笑,常因希望總是破滅吧?但有史以來,理念能變成現實的機律有多少?身後最有影響力的哲人,生前泰半都活在無盡的黑暗裡,許多人到死亦不見得有翻身叫板的機會。即使後來舉世推崇,卻常被人以他們生前最討厭的模樣, 去推崇自家對其理念的扭曲。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乃與希望相同」。人所以絕望是因為有太多太大的希望,若碰得頭破血流,首先就不該是懺悔,也不是「死雞撐鍋蓋」,更不是絕望,而得檢討所謂的「希望」是否虛妄。顧頡剛說做學問只求真不真不求用不用,人其實是不必在乎世人是否認可的。辛詞說:「青山欲共高人語,聯翩萬馬來無數,煙雨卻低回,望來總不來。人言頭上髮,總向愁中白, 拍手笑沙鷗,一身都是愁。」若熟悉宋史,便知像作者身處的當下,北定中原的「希望」,在現實的族群較量中,其實是沒勝算的。且後來宋家給滅了,胡笳遍野,天也沒塌下來,老百姓和文士還是照活可也,歷史還在前行,過若干年又是另一番天地。長遠看,杞人憂天只能徒乎奈何。辛詞成為千古絕唱,不在希望和絕望,而在於作者執著的心。執著是不必要現實向自家希望靠隴的。在最沒希望時,即使絕望也不悔,才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