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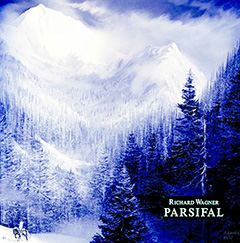
瓦格納的音樂雖開拓了一個新境界,但其人風評欠佳。許多書對他死前寫的《帕西法爾》有明顯的天主教傾向很失望,認為他一改無神論立場, 是向傳統觀念獻媚。甚至有說,是因為李斯特晚年當了神父,連帶其次女柯西瑪也對天主教熱中起來。此姝原是名指揮畢羅的太太,後來成了瓦格納夫人,瓦因受她影響而倒向天主教。但若細讀瓦格納寫過的文字,便知他其實不是無神論者,他確曾對信仰出言不遜,但這類語調是當時知識界中的激進分子的流行傾向,正如尼采在許多話題相當過激,未必即最後取態一樣。瓦格納始終是個路德教派新教徒,而本來是天主教徒的柯西瑪也沒有讓瓦格納改信天主教。因為天主教不許離婚,柯西瑪要和前夫畢羅離異便只能跟著瓦格納一起改信路德新教。不但他們的結婚儀式由路德派牧師主持,且柯西瑪的改宗也鄭重其事的擧行過新教的「重生」儀式。而這對夫婦在1870年的德法衝突中堅決站在普魯士一邊,表明反法和反天主教的立場,對晚年的李斯特也相當冷淡,甚至瞧不起他的音樂的簡約走向,認為他落伍了,只是個過氣巨星。瓦格納常過橋抽板,識於微時幫過他的人幾乎最後都被恩將仇報。這也難怪,一個自視太高的人很難接受自己曾需人提㩗,與昔間拉過他一把的人反目成仇便不出奇。但藝術家的作品及其灌注的心神與私德不能混為一談。此人一生的作品都企圖調和基督教與北歐蠻荒信仰,早期歌劇《唐豪瑟》就表現得很明顯。他在信仰上雖不住搖擺,最後還是大致站回正統歐洲信仰的立場上。《帕西法爾》有一種寬宏博大的屬靈氣象,有說作者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不過分的。
《帕西法爾》可看作是瓦格納臨死前對世界的最後盤問,是對人間信念追尋深層底蘊的最後感嘆。他原是個熱血者,但熱血之後,終其一生,最後也沒看到原來的熱血該在何方寄託。從許多記載看,我猜,他是悲哀的。從《帕西法爾》我們感受到,這是個差強人意的世界,但世界和我等是可以有救贖的,前題是,我們都得有一顆悲憫和純真的心。《帕西法爾》裡令人動容音樂,是否就是他對人間至善至美即救贖恩典的嚮往?若按瓦格納的那套從啓蒙思潮和北歐異教神話構成的浪漫主義世界觀去看世道,在終極的框架上,若多深思追問,他怎能自圓?最後返回傳統的框架中去, 未必是虛偽,更未必是倒退。他自視太高,其實只是個音樂家,只能寄望戲劇能給他自己,給觀者一些在不幸人生和紛爭世界裡一點希望,一點慰藉,後人又何必以大思想家的水準來要求他呢?歷史和現況中,不是有許多一生持不可知論的哲人(如花了一輩子寫了十大卷《文明的故事》的威爾杜蘭),死時接受了最正統的臨終聖禮,把一己卑微的靈魂,託付給冥冥中照看著這世界的不可知力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