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柏金遜」的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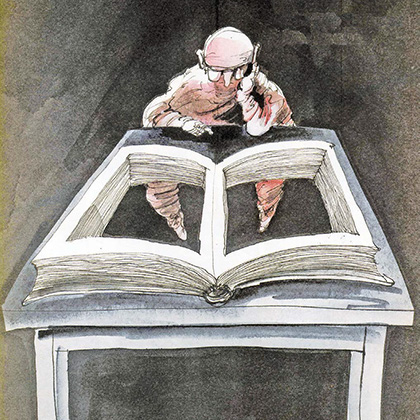
讀腦科新知,有說人睡眠是為忘記,深有同感:我們每天面對無數瑣事,還讀進許多高論和世態,若一一記住,腦袋豈不擠爆?現代認知論告訴我們,被忘卻了的瑣細鏡頭並非全然消失,而給壓進心底裡的無意識海洋,一有機會便會給翻出來,拼湊成令人費解,但內裡自有乾坤的夢境。文化人筆下的文思甚或意象,最內在的折騰常和這有關。而我們每天讀進的訊息雖枝蔓繁雜,其內在邏輯常修正我們的思維框架。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意識形態無不集淺薄思維大成卻仿如天條, 但人若愈曉得尊重真相,便愈不容易隨大流。不識時務的書呆子那顆常令當時得令的意識形態持份者討厭的「花崗岩腦袋」,便是這樣鍊成的。
兒時聽老師說,做學問得養成讀書寫摘要的習慣。成大學問者做的讀書摘要積累下來常比著作手稿還多,而許多皇皇巨著,都立足於這些摘要上。做摘要不盡是怕忘記細節,而是希望通過寫摘要,把握前輩高人的思維框架。所謂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是讓高人的深層經驗變成你的東西。有些人過目不忘,一目十行,不是記性特好,而是對自家專長的範疇前人知道甚麼了如指掌。而這範疇內一般的書,獨特新發現篇幅其實不多,其他論述難免是老生常談,可草草帶過,只留心那幾頁特別的即可。我信老師的話,年輕時確認真地讀了許多書, 記憶最深的是廿歲出頭那三年,在囹圄中把黑格爾的《小邏輯》和馬克思的《資本論》對照著讀。每章讀十來遍,直到全弄通了,逼著自己用自家的語言簡述,特別留意這兩本書的框架如何轉化,即留意黑格爾對馬克思有何意義?當時書店只賣毛語錄,其實也無書可讀。而我得這樣讀, 是因為思路走到瓶口,不弄清很難心安理得。一個人人可得而魚肉之的「反革命」讀這些書當然惹人側目,卻無人能找到理由聲討,但我由此學懂了用這兩位老人家的想事方式看世道。現在回想起來,當然相當滑稽,但這些年的陸離世事哪件不滑稽?後來我跑到外頭,可讀的書太多,也不可能再像當年那樣啃書,讀書常只有睡前的邊角時間,往往第二天早上,常連昨晚讀過甚麼都記不起來,我對這水過鴨背的狀態也聽之任之。我雖也寫書,卻不是學苑中人,不用引經據典,即使讀最了不起的書,過後細節全忘,我信讀進去的東西自然會在深層意識中和原有的框架不住調合衝突,不住把框架修正。只要框架大致完善,碰到要討論的問題,即使能把握的只是最尋常的材料,也容易發掘出我該說的。
但最近我嚇了一跳:我想解答某個問號, 重讀三個月前讀過的一本書,竟發覺像讀一本從未碰過的書那樣全無印象。我是失憶了嗎?柏金遜症患者不乏世上最聰明的人,且有些患者才四十來歲。中六合彩不易,病魔臨門卻不必擇日,若真個如此,我是否死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