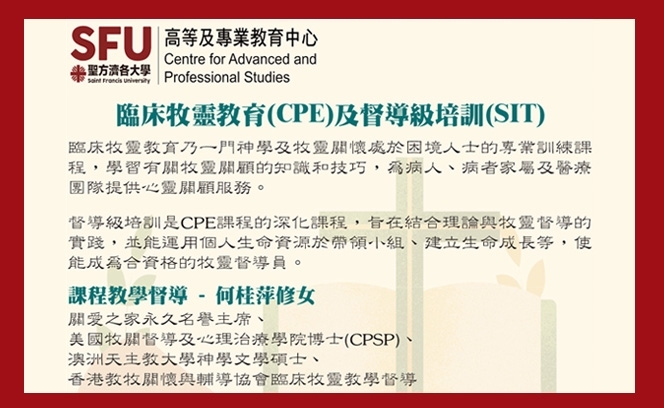【在人間】浪漫和語言

人最了不起的發明是語言。有說語言的發明是為溝通,當然對,但溝通甚麼和怎麼溝通,內裡便大有文章。語言的出現和發展常伴隨著主體意識由微弱到膨脹,人由蒙昧到開竅,發現自己是這麼一種生靈:他擁有語言,而事物和其他生靈在其語言標簽下可對自家顯現為某種東西,仿佛所有身外之物都逼切盼望受自家的指稱和談論,而自家的語言似乎有巫術般的魔力,能給萬物定性。於是人便成了萬物之靈,仿佛在大自然之上架起了一個能展示自己的舞台,若自家不存在,世間萬物便只能緘默無語地沉入無邊的黑暗中。宋儒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若無聖賢(包括他們這些後學)光照,宇宙的存在還有甚麼意思?
時下愛說溝通,但溝通常不是平等、善意地取長補短互通有無,誰是主體誰說了算往往最茲事體大。在這充滿紛爭和自以為是的世界,語言常是佔地盤的投槍匕首,其意義常在於建構一個大寫的「我」。世界充滿奧秘和不確定性,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人除非有大智慧,總愛把一切放在掌心,熱衷給不懂的定性,給不可知之物命名戴帽,以便分清敵我,動員一切力量置之死地或捧上雲端。各式早期宗教都設定了自家一廂情願的最高存在,談論自家供奉的神仿佛便把握了宇宙奧秘,這想象中的共同體共同想像的終極意象,其實只是無意識在投射。但無意識終究要化成可供談論的意識,於是每種意識形態都有其烏托邦,都偉大無倫,可惜不過把話語系統的「原概念」具像化。但誰都知道,說某物本該如何不等於實在如何或曾經如何,把三者混淆,不過是把所談論的真實世界浪漫化的話語遊戲。
現實當然半點也不浪漫,但這不妨礙, 指鹿為馬者常以浪漫目光掠過如鉛似鐵的真相,去給自家的密底算盤渲染出某種浪漫氛圍。德國哲人薩弗蘭斯基有本很出名的書, 中文譯做《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劈頭引用的是十八世紀末詩人諾瓦利斯的名句:「當我給卑賤物一種崇高的意義,給尋常物一種神秘的模樣,給已知物以未知物的莊重,給有限物以一種無限的表象,我就將它浪漫化了。」詩人也許是最專業的浪漫製造者,但浪漫不是詩人的專利, 任何凡夫俗子都可以是浪漫高手。而浪漫最泛濫的是情場,最樂此不疲的是政圈。愈庸俗的世道情歌式囈語愈層出不窮,而政客在明刀明槍地欺詐的同時,也決不缺浪漫說詞及自製美麗光環。西諺有道「浪漫是以欺騙別人開始,以欺騙自己告終」。行騙者說得多了, 最後往往連自家也信以為真,看圍爐取暖者常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堪稱一絕。
在這咀砲天天在耳畔轟鳴的世道,細細咀嚼諾瓦利斯的上述名句,常不禁會心一笑。有說被充份解釋的世界是給淘空的世界,變得狹窄,直至成為囹圄。不久前才逝世的符號學大家艾可說,人發明語言是要用來說謊,這話說來雖不免悲哀,卻充滿由古到今不乏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