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真」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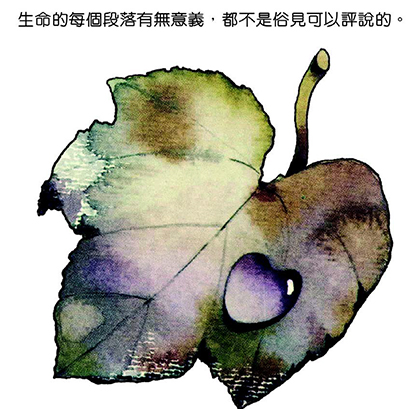
(續上期)教兒子如何持弓運腕,控制好音色的那位老先生也是著名樂評人,每有重要的音樂會和唱片問世,他都替我們把門票和CD訂好,於是每個精采的音樂演繹到底好在哪裡?我們聽到的,便不是人云亦云的空話,而是老資格內行人實實在在的體驗,兒子獲益匪淺,連我也大開眼界。前些日子才知老人家過身了,當年在他家受教的情景,尚歷歷在目。
但最後,兒子和大多數同期學琴的同學一樣,都沒有唸音樂學院。老師對他說,你和我一樣,有音樂感卻沒表演慾,縱有一百分水準,一登台便只剩下五十分。表演慾強的人本來只有五十分功力,登台常擴大成一百分。簫邦就是只合在朋友中低吟淺唱,一到大場面便失控的人。那時音樂會的規模通常不大,觀眾著意的是內涵,不像如今,演奏家拼搏的是炫技性質的了得。於是時下要在樂壇出頭,在著名大賽奪魁幾乎是唯一途徑,參賽者有如奧運選手般搏殺。你我都不是這種料子。我是過來人,不建議能唸好書的學生選擇以音樂為業。音樂其實是「玩」才有意思的,成為飯碗和要爭要鬥就未必有趣,何況這口飯也不好吃……
兒子聽了,如負重釋,有空照舊練琴,結果很輕鬆地進了港大,本科唸哲學,碩士唸心理。我也難得糊塗,他選甚麼學甚麼,我從未給過意見,是他把一切都按自家的興緻「搞定」了,才告訴我的。親友中有不少人問:小時花了那麼大的氣力學音樂,豈不是白費了? 我也不作解釋。看著他能對著總譜聽唱片,帶著小女友看歌劇,到歐洲公幹時可和同事去聽室樂……閒時還會對柏拉圖佛洛伊德等說過的話題幽上一默,且還可以在工作中有條不紊地處理許多理性爭端或非理性糾結,便想到音樂豈止是音符?燕雀鴻鵠,脣舌何涉?
人其實是不必理會「學了有甚麼用」之類的「老土」問號的。我自己少年時是學畫出身的,為了學懂人體結構和如何讓自已有良好的造型能力,床底下放著一箱子骷髗,有空便拿出把玩。到如今我還可以隨手畫出各種動作和角度的人體骨骼和肌肉結構,都拜少年時的苦學所賜。但當時只是好奇,只渴望自家有想畫甚麼便能畫出甚麼,想怎麼畫便能怎麼畫的能力,並沒有想過學來有何用,更不會想到可拿來混飯吃。甚至當興趣轉移之後,有過許多年,我居然忘了自己能畫畫。那時在傳媒爬格子,有次老闆著我登報找人畫插畫,結果無一滿意,才想到不如自家動手,結果是一試即合,才令同行知道要畫東西可以找這個人。我也不相信人學了甚麼最後終歸有用,世事的結局未必是終局,你可以去找原因,但許多所謂的因果常出於隅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經常發生,說明了世事的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果, 不會少,不會多」,常只是善意的想像。人都愛說「有志者事竟成」,但即使事成,原來的「志」既未必光彩,「成」的也未必是好事。顧頡剛說「做學問只問真不真,不求用不用」是相當對的,為書呆子,世上唯有「真」是值得存在的。「用」常只是俗見,不提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