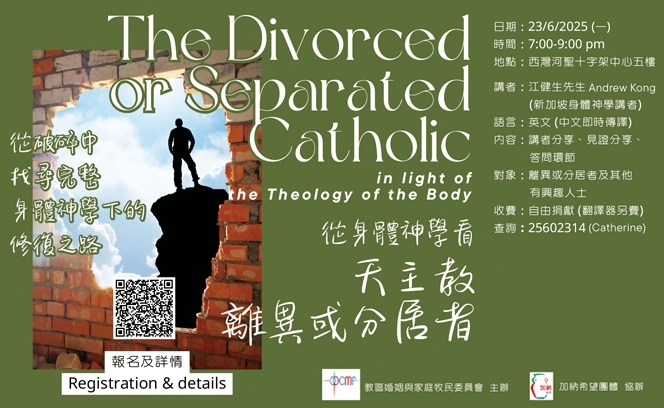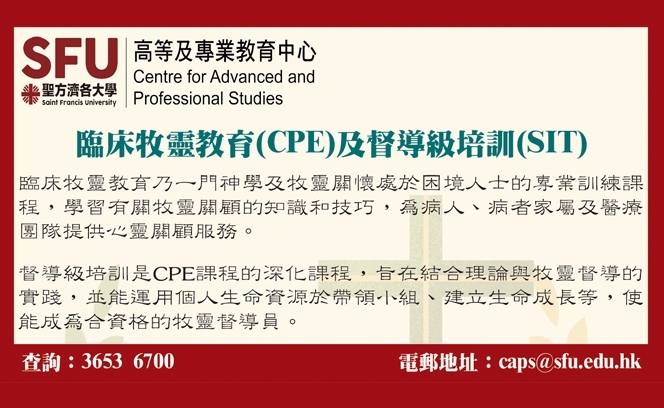懷念俞桂芝修女

香港好友從微信中告知我俞修女回歸父家的消息,難過傷心之餘,多的是悵然若失,無奈身在遙遠的彼岸未能親睹修女最後面、送她一程,永遠是一個遺憾。
今夜月滿高掛,躺在床上,又是無眠的一晚,與俞修女相交相知超過半個世紀,昔日情景一幕幕重現腦海。一九六四年因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離島長洲官校初中二,轉到了九龍名校聖瑪利嘉諾撒中學高中一年級,俞修女正好是當時中文部的校長。
畢竟兩校在某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距離,故此俞修女對我學習方面甚是著緊,怕我少讀一年課程趕不上,還有在新環境、陌生的同學間相處等各細節都伸出援手、鼓勵和開導,與想像中嚴肅不苟言笑的校長形象截然不同,既和藹又親切,這是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三年的高中轉眼又離歌高奏,大部份的同學都投考師範教育學院、護士培訓等較適合女性的行業,可惜當年我未足十八歲,報名被拒諸門外。眼見暑假後同學們都展開新一頁,自己卻呆在家中斯人獨憔悴,雖然後來廣華醫院的護士培訓班免試取錄(因為會考生物科成績優良吧!一笑)但仍要等到翌年生日後滿十八歲才可以入讀。在這段真空的日子也得到修女的開解和安慰。直至我另找到銀行的工作,放棄等待護士的培訓,而修女也被調回澳門工作,見面、通話才少了,改為魚雁互通。
俞修女是一位極孝順的女兒, 年中只要能抽到時間,都會乘船來港探望住在香港仔安老院年邁的母親, 其實當年修女已年過七十,獨自一人長途跋涉從澳門乘船來香港,再乘巴士到香港仔,還要携帶半打俞媽媽特別愛飲的罐裝可樂汽水,真的不容易呀!因事緣有一次我休假,到港澳碼頭接她,陪同到老人院,才知道甚麼叫舟車勞頓。
我在銀行工作廿八年後,機緣巧合,找到了一份更適合我做的工作, 就是到尖沙咀玫瑰堂當堂區秘書, 在辦公室可以遙望到當年上課的班房,而俞修女也曾在玫瑰堂教過慕道班,當時也來此探望過修女,所以當一九九五年某一天,俞修女不聲不響的出現在我辦公室,給我一個意外驚喜:喜的是她不遠千里來探我,讓我可以再次擁抱這位慈祥、痛錫我的長輩,驚的是她一位老人在路途上的安危。
做修女就得聽命服從長上的調配,這回天從人願,修女也回到堅道總修院服務,我以為我們又可以常見面了。誰知一場八九民運,遠在美國的妹妹不放心我在香港,因此為我一家申請移民。一九九九年又得和俞修女分隔兩地,偶爾返香港必定到修院探望修女,一敍舊情,時她的頸骨無力,頭垂得很低,矮小的個子顯得更細小,她竟能幽自己一默的說:「我喜歡低頭思故鄉呢!」我相信她如今已在天上的家鄉了。二○○四年回香港是修女最後一次和我促膝而談,當我知道她在二○○七年中風後,第二年回來探她時,她已卧床、不言不語、眼睛也沒有張開看我一眼。但我感覺到她會聽到我對她說的話和唱給她最喜歡聽的「花地瑪聖母」歌,因為我看見她眼角滲出滴滴淚水。
致俞修女:「你這十一年卧床的日子是怎樣捱過的呢?千萬不捨,也得承認這是為你最好的結局,相信你在天之靈也不會忘記我這個不成氣候的學生,正如你也知道你永遠在我的懷念和祈禱中。親愛的俞修女,你知道我在想你嗎?」
•寫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