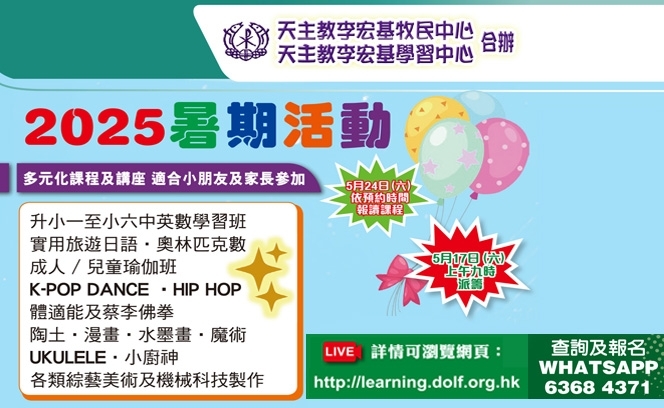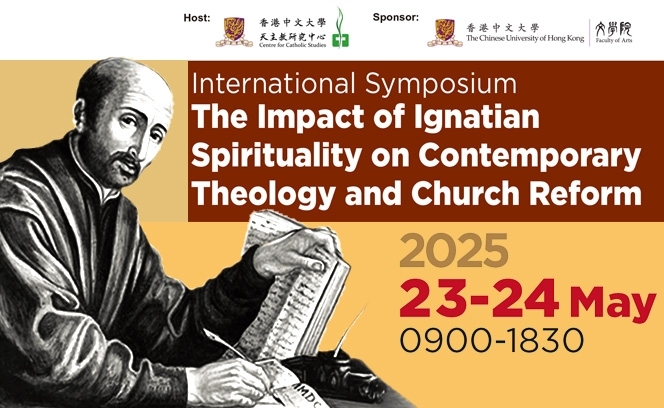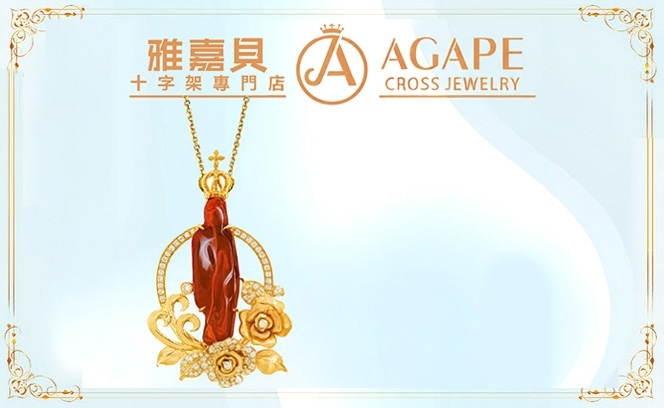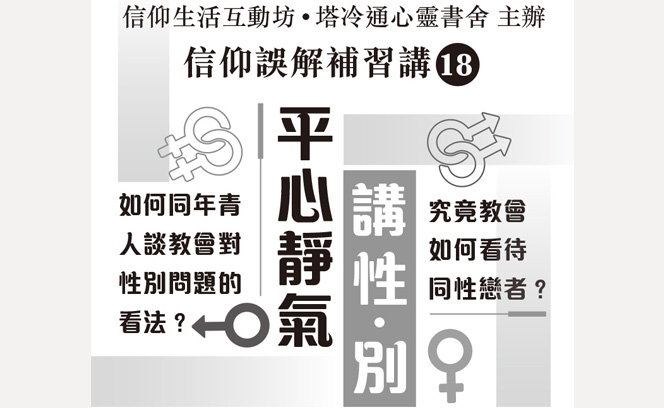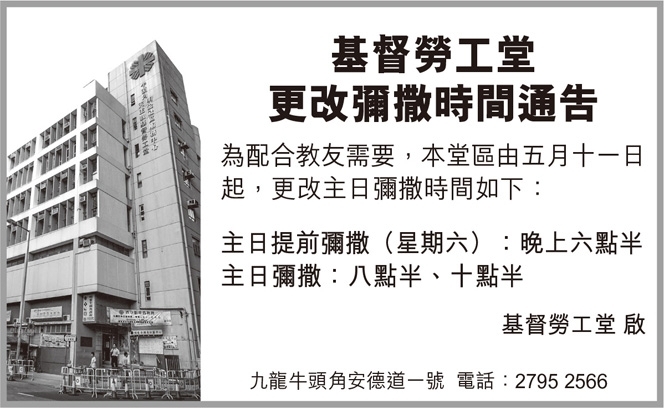【在人間】四月裡的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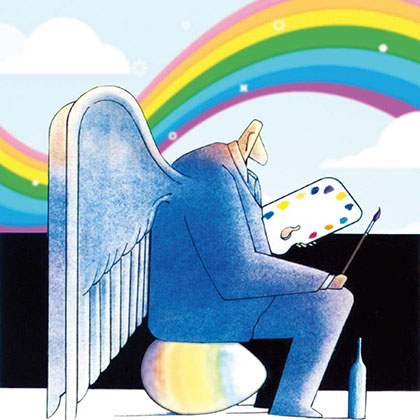
四月前有清明節,後有復活節,都與死亡有關。清明本是廿四節氣之一,這段日子嚴冬已去,天清氣明,萬物復甦,古時帝王「墓祭」和民間祭祖都在此日。為甚麼生和死要一起紀念?是因為先民知道有生必有死,若不想把死亡這人人都逃不過的終了視作悲劇,便得讓有限的生命衝破現實的制肘,和萬物萌發的春天聯繫起來,好讓生和死聯結成生生不息的更新,否則人生豈非一場敗績?在西方文化中, 基督徒的復活節本和猶太舊教的逾越節分不開。逾越節本來就有個衝破死亡的故事,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給人間帶來復活的希望,是老信仰萌發的新枝葉,而Easter一詞來自北歐的春天女神 Ēostre,四月本以她命名,基督教盛行後,異教節日的春天色彩被轉化成復活節裡讓人間充滿希望的新生意象,與聖誕節異曲同工。近世學者愛把西方文化的源頭稱為兩希文化(希臘和希伯來),復活觀念孕育的母體是猶太信仰,但古希臘文化其實也早有協和:酒神狄奧尼索斯崇拜遠比奧林匹斯諸神崇拜更古老,酒神本乃春神,衍生的俄耳甫斯教的信仰核心是神能死而復活……和清明節可追溯到國人遠古時有關生死的智慧一樣,復活節也薀含了中東和歐洲諸文化的古老心靈經驗的沉積。
近來愈來愈覺得要把自家的許多窘惑弄清,最好回頭把人類由古到今的重要書本重讀, 愈讀便愈覺得,對人生和人性奧秘的思考,總是伴隨著面對死亡開始的。《柏拉圖全集》多從〈申辯〉、〈克利托〉和〈斐多〉三篇開首,說的是蘇格拉底受審和面對死亡的故事。可以理解,老師的橫死充分顯示了哲學和政治的不咬弦,這對柏拉圖的衝擊有多大?但前兩篇是柏拉圖早期的對話錄,寫後一篇時柏拉圖已步入中年,筆下對人生和死亡便有更深的盤問,因此〈裴多〉和前兩篇並不處於同一層次,讀來自然對蘇格拉底心中的「底牌」理解更深。〈理想國〉是同一時段的作品,也是柏拉圖最重要,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扛鼎之作。這書雖近四百頁,說的卻只是蘇格拉底和朋友在同一天裡的對話。而這場二千多年前的辯論,交鋒的各種論調我們都似曾相識,彷彿預演了後來史上許多著名的形上爭拗,其中好些還太像時下隳突叫號振振有詞者的炎炎大言,可見人類愛奉正義之名捩橫折曲或坐井觀天者中外如一,歷二千年而不變。讀這書,看著許多「意見」被蘇老頭子剖釋得入木三分, 令人想起時下盛行的種種歪理,如魯迅說的「壞人靠著冰山」,不禁莞爾。而這書也讓我們看到作者一個潛在的致命傾向:理想主義者一想主宰現世涉足政壇,理想國便變成如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農莊》,這可不是我等比柏拉圖高明,而是及後兩千年的教訓令最蠢的人也得聰明起來。
這書發人深省,以一位事業有成卻行將就木的老紳士的心裡話進入主題:人快要到另一個世界去時,定為自己曾做的事膽戰心驚。自己行的都正義嗎?我們會面對正義的審判嗎?但,甚麼是正義呢?不同人有不同回答。就這樣,柏拉圖開始了他的大哉問。蘇格拉底答對了嗎?乍看他是對的,看深一層其實卻未必盡然。可以說, 這盤問直到今天也沒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