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首鼠兩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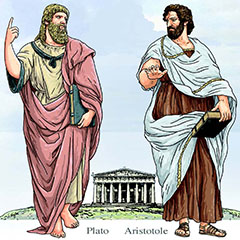
在柏拉圖對話錄中, 《克利托篇》緊跟著《申辯篇》。克利托是蘇格拉底的朋友,力勸他逃亡:既然城邦對你不公, 何妨一走了之?蘇卻說了一段和法律的對話:沒有國家可以無法規存在,任何國家的第一條法規是公民不能逍遙法外,選擇他們想要服從與違抗的法規。任何違抗不僅是質疑那項法規, 更是質疑法律的本質,質疑所有法規。質疑或違抗法律等同於摧毀法律的權威,而公民的存在歸功於法律,是由法律所創造與促成的,其運作對我們任何違紀行為有父權看顧般的威信,值得尊重與孝敬。 蘇老頭子的邏輯不無道理,卻有無限引伸兼誇大之嫌,於是在我們面前便出現了兩個蘇格拉底:在《申辯篇》中,他面對死亡威脅也不放棄原則, 呈現的是哲學家對抗城邦的論點;《克利托篇》則反過來,呈現的是城邦對付哲學家的論點,將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及處決視為伸張正義的範例。兩篇對話錄代表著兩種無法調和的道德規範。前一篇,公民信賴自己的理智,遠離未必健康的國家權威,守護個體不與不義合流的良知;後一篇認定絕對服從是每位公民的義務,官方意向被理據化為城邦集體意志,不許不同意向者說半個不字。 前一篇蘇漠視死亡,但在後一篇,他漠視死亡的勇氣只表現為拒絕讓克利托助他逃亡,為正義挑戰威權的底氣無影無踪。柏拉圖為何首鼠兩端?
蘇格拉底直到最後似乎都保持著一種自我定義的法律。我們千萬別忘記,柏拉圖是個道德主義者,把蘇格拉底面對的兩難納入道德框架,其慷慨赴死乍看求仁得仁完滿收場,卻掩蓋了在實際政治生活兩種取態的嚴重衝突。柏拉圖和孔子一樣,慣於以道德盤問來處理政治問題,難怪他最了不起的學生亞里士多德頗有微詞,寫了《政治學》一書,填補乃師的真空地帶。也令人想起漢娜.阿倫特如何寫《平庸之惡》:一九六一年,以色列法庭有一宗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受審者艾希曼是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納粹倒台後,他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他自辯說自家無罪,當時在德國,元首的話就是法律,他只是個守法的人,一切行為都只在履行職務。阿倫特說,艾希曼如能假設自己是猶太人,就會說:「我是德國猶太人,在這裡住了一輩子,跟其他德國人具有同等的居住權,政府無權剝奪我的公民身分、工作、甚至性命。」但他沒有這種同理心,而追隨當時的主流偏見:既然政府說猶太人不是德國人,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猶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道聽途說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大多數人不思考,即縱容集體的瘋狂,把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更有甚者是不少人竟和當局合作,事後卻說自家逼於無奈,二戰中猶太領導人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但不管你在道德上如何自圓,只要你參與了執行,你就要負起責任,就是有罪。法官應該有勇氣說: 「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你實際的作為,而非就你內心和動機。即使你成為這個大屠殺組織的一個工具是出自壞運氣,並不影響你執行大屠殺的事實。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就要負擔責任。」
此書當時有許多爭議,幾令作者眾叛親離,但對的顯然是她,也讓我們對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取向的兩難有了個把抽象爭論放回真實世界的理解。不慣鑽書堆者不妨看看Now TV常重播的電影《真理無懼》(英文名Hannah Arendt),說不定會燃起一讀此書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