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千古艱難唯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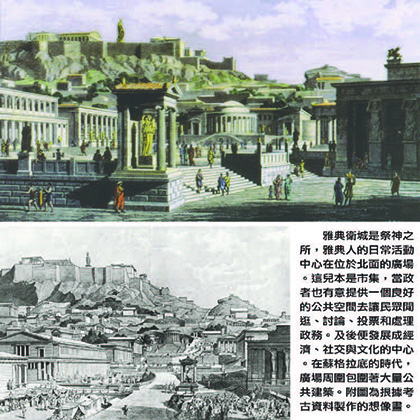
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認為不同政制會造就不同人格: 理想的政制造就善者和正義者。斯巴達的軍國主義政制造就好勝爭強,追逐榮名者。寡頭政制造就愛財,寸利必得者。民主政制造就平等主義者。僭主政制造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者……在這比較中,民主制排名不高,但比僭主制好。有的書據此判定蘇格拉底敵視民主,其實未必。蘇格拉底首選的政制當然是他的理想國,但此制既在人間子虛烏有,可放下不表。而在上述評說中,他對斯巴達和寡頭政制其實也不見得有太好的評論,看來二者和民主制一樣,都不理想,未必對造就國民的品格有益。斯巴達武人當道和寡頭制唯利是圖,不過是民主制之外的另兩種可能性的選擇。而民主制當時在雅典不是一種可要可不要的選項,而是雅典以往政經歷史積累下來的自然常態。「常」到甚麼程度?古希臘人視「正義」與「自然」同義,和中國文化原意一樣,「自然」即自然而然,如水之就深火之炎上般不證自明。眾人之事該眾人參與,提防大人物化公為私,為雅典人是天經地義。蘇格拉底雖對世風批評多多,重點側重於政客缺乏智性的誠實和著迷於強權政治,大眾自以為是,只注重物欲不關注靈性德行等等;而一涉及思想自由和獨立自主,他從來都理直氣壯。這說明,民主制正面意義的開放性質,為他有如人得吃飯呼吸一樣自然。他不接受的是其負面:民主制不錯使雅典人意氣風發,在地中海沿岸如鶴立雞群,但交的學費太沉重。民主常迫走自家的忠誠衛士和英明領袖,萬事交由投票甚或抽簽決定,形成多數暴力,讓大轟大嗡的烏合之眾決定城邦命運……雅典其實真可謂「成也民主敗也民主」。但歷史上並無一種令人信服的大敍述敢說人類該消除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夢想,都傾向考慮怎麼把公權力關進理性籠子,讓它既管好一切,又受大眾和社會的監督約制。現代代議制就是這麼一種並不完美,卻有很大改善餘地的實驗。
批評民主制的人不一定是民主的敵人,可惜民主派中好些人極權主義味道甚濃,視蘇格拉底為敵便理所當然。他其實不是政治人物,著眼的只是人品和社會的道德風向,對制度改革沒有興趣。他所做的, 其實是在宣告,人類因著理性可相互交流,前提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自他開始,人不再在威權前唯唯諾諾,敢為真理發聲便成為無須爭辯的正常活動。
推翻民主制度的三十僭主,蘇格拉底三個學生阿西比德、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是要角,後兩人是柏拉圖的舅父。柏拉圖晚年說,那時民主政權為一般人厭惡,政變發生,他被邀參與政事。那時他年少天真,以為雅典可借此一洗頹風, 但那些新上場的紳士們的一舉一動,卻讓他們毁壞了的民主政權反而變得像黃金時代。結果民主派反攻並取得勝利,他兩個舅父都在戰鬥中喪命。在僭主當政時,蘇格拉底拒絕合作,若非民主派復辟成功,他定然死於僭主刀下。但諷剌的是,民主派一上場,他便被入罪判死。重新得勢的民主政府指控蘇格拉曾教導過上述三個對國家犯下滔天罪惡的敵人。也許學生的背叛令蘇格拉底深感不安,但他不是也有學生因支持民主而死嗎?若他出逃,人們就會認為他是民主政府的反對者,只有留下來,才能證實自己從不是國家的敵人。也許他會認為,忠誠的最好證明莫過於願意為國殉難。古詩有道「千古艱難唯一死」,珍惜名譽者選擇「與其苟活,不如就義」,亦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