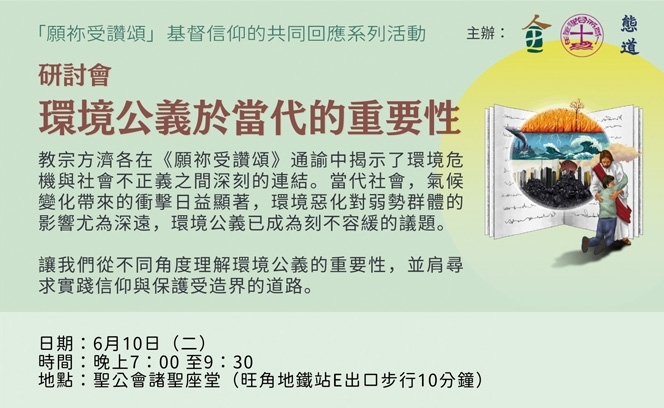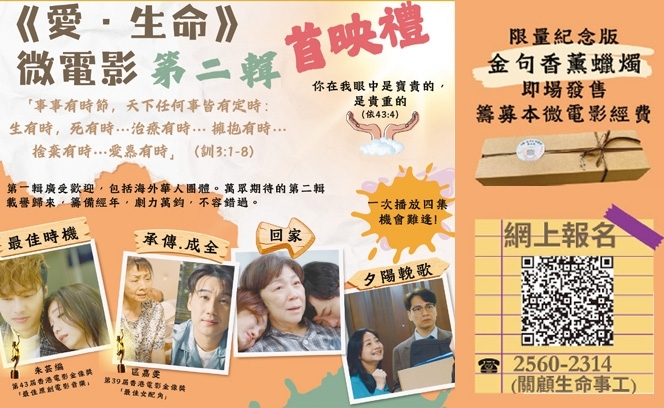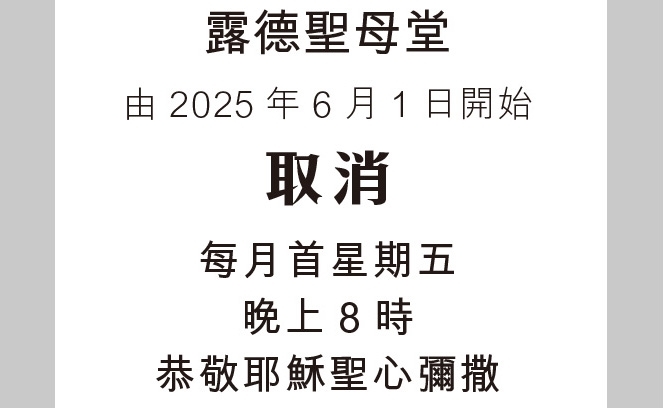【在人間】進得去 出得來
 黑格爾的書裡有個概念叫「異化」,認為映入我們眼簾的萬事萬物,包括大自然, 都是觀念的客觀化,即人的自我在「異化」。這話說來深奧,實不難解: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尤其是人類文明的架構和行為,無一不是自家心靈需要的投射,可視為我們觀念的外在化。而這些衍生物本來都因應我們的需要而產生,一經問世,便會獨立自主起來,終有一天成為自在自為的東西,疏離了它原本的規定性,異化成獨立王國,反客為主,反過來主宰我們的生活和觀念。柏拉圖在《理想國》裡討論了當時幾種不同的政體,比較其優劣和所造成的子民德性,令人很容易便想到黑格爾說的「異化」:國家機器本是城邦公民為管理自家事務和福祉而建立,一旦出現並運作,難免膨脹成官僚機器,獨立於公民的意願,變成可吞噬一切的怪獸,社會的公僕也由是變成社會的主人。類似的「異化」,古今中外哪天哪處或缺?
黑格爾的書裡有個概念叫「異化」,認為映入我們眼簾的萬事萬物,包括大自然, 都是觀念的客觀化,即人的自我在「異化」。這話說來深奧,實不難解: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尤其是人類文明的架構和行為,無一不是自家心靈需要的投射,可視為我們觀念的外在化。而這些衍生物本來都因應我們的需要而產生,一經問世,便會獨立自主起來,終有一天成為自在自為的東西,疏離了它原本的規定性,異化成獨立王國,反客為主,反過來主宰我們的生活和觀念。柏拉圖在《理想國》裡討論了當時幾種不同的政體,比較其優劣和所造成的子民德性,令人很容易便想到黑格爾說的「異化」:國家機器本是城邦公民為管理自家事務和福祉而建立,一旦出現並運作,難免膨脹成官僚機器,獨立於公民的意願,變成可吞噬一切的怪獸,社會的公僕也由是變成社會的主人。類似的「異化」,古今中外哪天哪處或缺?
有文明便有建樹,也必有異化。異化不一定是壞事,黑格爾說到它時也不帶褒貶。由是想起二十世紀的音樂新風,不就是如此這般地發展起來的嗎?荀白克無疑是這風潮的主將。其早期作品很有布拉姆斯風味,充滿德國晚期浪漫主義氣息,並開始把以瓦格納為代表的半音化技巧發展擴大。這時期他寫的大型清唱劇《古雷之歌》,要動用五位獨唱家及一位朗誦旁白者, 加上三隊男聲合唱團、一隊混聲合唱團及近一百五十位樂師的管弦樂團。單是弦樂手,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各要二十人,二人一組各演奏十個聲部,簡直是迄今為止正統音樂的巨無霸。此曲歷十一年才完成,看來作者在正統路上已走到盡頭,才開始把調性拋棄,跟著便發明十二音體系,把音樂語言徹底轉換。 但音樂史上此事彷彿早有預謀:和聲一直不住演化。最初主流音樂為單聲部,直到奧爾加農問世才出現複調,但只有純八度和純五度被認可。到中世紀末,三度、六度及純四度才出現,但縱向結構上純五純八度音程仍然為主,且佔穩強拍;三度、六度和純四度這些被視為「不協和音程」只能出現在弱拍,後來才可在多於二聲部的音樂中出現在強拍上。但是增四減五音程仍只可出現在弱拍,大七度和小二度仍不可用。巴洛克和古典時期大致沿用了這規矩,在十九世紀中葉發展到頂峰,其後出現各種新技巧。瓦格納開始使用十二音,德彪西作品也出現大量非常規技法,但仍相對地尊重「調性」。荀白克去得更盡,將音階內的每個半音都賦予同樣的意義,完全脫離「調」的概念,回歸到以「音程」為主的寫法……瞧,音樂就像許多人類事務一樣,每個範疇只要一成氣候,便會獨立起來,異化成自把自為的東西,完全按自家的邏輯行進演化。專業者沉醉其間,早就忘了「初心」,視大眾品味和需要如無物。愈寫愈高端的音樂成了純音樂,是小眾的高雅遊戲。就音樂而言,確反照了我們時代最深層的精神風貌,妙不可言,令人擊節。可惜聽眾要得其門而入,不至暈頭轉向, 並不容易。這也許是必有之惡:要看懂讀懂聽懂這世界,誰不需付出高昂代價?世上有哪門學問或藝術是人生下來便懂的?政治和哲學又何嘗不如此?每門學問都可以是一個牛角尖,都可自成一角。想有所得著者不是逃避這一個個早已異化得令人不敢狎近的領域,而是要進得去,出得來。莊子說「得魚忘筌」:把竹器(筌)投進水裡是為捉魚。無「筌」是捉不到魚的,但捉到魚後還要不要「筌」,則無傷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