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我們該「唯」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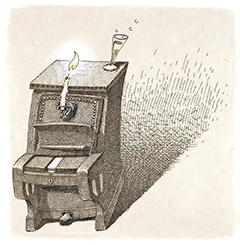
坊間的書談哲學,下筆伊始常先區別「唯物」與「唯心」。唯物主義說物質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按十九世紀的流行觀念,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物質,連精神也不過是物質性的肉體在生命未結束前的某種科學暫時解釋不了的現象。於是便給人錯覺,彷彿一宣稱自家崇尚「唯物」,所說的一切自然便都客觀、科學得很。殊不知人無論宣稱自家的思維方式的前設「唯」甚麼,總脫不了用語言即概念去思考和傳達,所思所說的其實不一定是「客觀世界」,而是說話者用習以為常的語匯組合的指代,是說話者頭腦中的客體而不一定是真客體。宣稱「唯心」或「唯物」,其實都可以主觀得要命,怎麼把概念編織推敲,可充滿隨意性。
黑格爾學說不是被稱為「客觀唯心主義」嗎?讀過《資本論》的人很易得出這麼一個印象,馬克思這皇皇巨著是以黑格爾的邏輯學為框架的。其所謂「唯物」,是作者把黑格爾邏輯學中的「有」與「無」的對立統一,轉換為資本主義大生產中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統一,兩人都以一對元概念的矛盾來展開整個現象世界。黑格爾是觀念論者,用唯物主義觀點看,「唯心」得很。若把黑格爾哲學體系視作以頭倒立的世界,馬克思的批判便等於把顛倒的世界重新顛倒過來。但請注意,即使馬克思如何「唯物」,還得使用自家腦袋裡的概念去思考現實世界中有關資本主義大生產的一切。而他思考的每一步是否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真相相符,他說的是否正確?有待他以自家的學說去證實,得讓行家檢討其立論和推論是否在理, 所根據的數據和社會調查是否公允,並非因他宣布了自家「唯物」便不證自明。是以他死後,許多有識者猜測,這老人家花了一輩子去完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卻從沒興致去寫一本辯證唯物主義讀本,像後來斯太林組織手下的意識形態專家寫的那本「獻世」之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那樣,其實不是疏忽。竊以為世事當然可分兩極,但走極端始終不如中庸。中庸不是折衷,而是合度。凡事一「唯」便很難不偏頗。既然「唯心」「唯物」都得用概念去思維, 「唯」甚麼的分野還值得強調麼?
唯物主義在歷史上曾被稱為懷疑論,笛卡兒那句「我思故我在」杜絕了懷疑論對哲學的所有質疑:因為我在思索,所以我存在。世上所有一切都可以是假的,懷疑者總該不能懷疑自家的存在吧?但思考的主體存在,不等於被思考的客觀世界一定存在。即使在思考者跟前真有個客觀實在的事物明擺著給他研究,思考主體一旦使用概念,所「思」的,就只可能是自家腦袋的反照。他的「思」所使用的語言和概念其實許多都互為因果,確實意思還有待考訂,雖然可以是真相的鏡象,卻不一定沒有偏見,甚至有些是立場先行或因情緒化而扭曲也說不定。即使思想者用心良苦去求真,所「思」出來的所謂「真」,既離不開思考者所在的那個文化環境眼下約定俗成的詞匯組合,所「思」的便決不一定那麼「客觀」,難免經過固有的那套意識形態過濾。
人都照過鏡,都知若鏡面正常,鏡象會離真相不遠;若鏡子有問題,端正的臉孔也會怪模怪樣。現世間同一件事在不同人和不同世界的描述中是非黑白可全然顛倒,說明了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