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官」和「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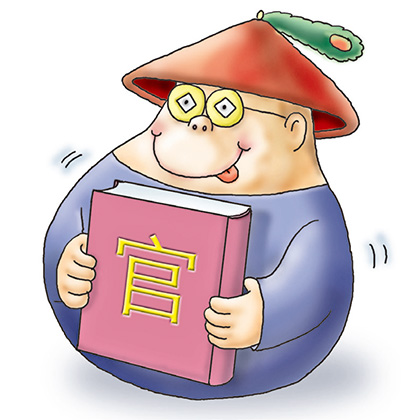
「吏」是文職官員,起初職責和「史」類似,因此甲骨文的「史」和「吏」是同一字。《說文》謂「吏,治人者也」,當時還有「天吏」一詞指「賢而在上者」,有若天使代上天管理人。甲骨文與《禮記》已有「官」字,漢以後才以此專稱高高在上的「大吏」,「吏」便專指下層的師爺或差役之類。「官」在甲骨文起初只有「寶蓋頂」,原意是「放兵符的房屋」,引伸為「掌權者」,加上「竹花頭」便是「管」,即掌控眾人。「管」亦即毛筆,可見「官」也好「吏」也好,都離不開寫字。有文字才有文書、律例,才有自上而下一桿到底的官僚管治。中國古代那種皇帝坐龍庭,皇權無孔不入的一統江山,全賴郡縣制文官系統支撐,基礎是漢字在皇權所及的地域(即「天下」)無遠弗届。古人稱玩弄律例, 以文字殺人者為「刀筆吏」,而甲骨文「史」「吏」同源,「史」原是「巫」,於是「官」和「吏」背後都有「神聖」光環。國人歷二千餘年始終揮之不去的「官本位文化」,其來有自。
吏治始於春秋,戰國大行其道,造就了歷史的新走向。人們見戰國兵荒馬亂,便咸以為夏商周三代是太平盛世,其實人類歷史何時沒有戰亂?上古時部落氏族林立,夏禹時據說有萬國, 即有上萬個部落來朝覲,周武王時只剩八百諸侯,春秋時只餘下一百多個,到戰國便只有「七雄」,最後給秦一統天下。「統一」即「兼併」,即大魚吃小魚,過程都血流成河。相應地,《孫子》成書比《老子》和《論語》早,也就是說,給中國智慧開篇的不是孔夫子的仁義道德,而是兵家心術,崇尚的是兵不厭詐,兵以詐立,機關算盡。國人愛說「盡人事聽天命」,後三字未必真有市場。唯意志論是那麼受歡迎,誰不「有風駛盡裡 」?
春秋及以前,「國」是貴族城邑的聯合, 由頂層到基層,各層級的城邑都由和君主同姓同族的貴族控制。城邑是貴族聚集的居民點,由青銅貴族武士守衛,操控壓榨著散佈得更廣的「野人」(平頭百姓)及小邑(低級貴族)。那時的戰爭著意的也常是誰能稱霸,誰與誰結盟,與誰訂立了怎麼樣的從屬關係。但隨著以鐵器、牛耕為先導的農業技術普及,在兼併中敗落的氏族流散四野,許多人失去氏族的庇護,成為孤狼般的個體,有才能者變成文士和俠客,只得一身牛力者變成佃農及自耕農,等而下之的是沒人身自由的庶子和居無定所的傭客,當權者也學會了直接向個人徵稅、徵兵,讓人人服勞役,削弱傳統貴族的勢力。實行新法管治的君主在競爭中更有優勢,便不滿足依靠世襲的親貴治事,只在直屬領地施展權力,紛紛建立能征慣戰的軍團和穩定的官吏體制,佔滿城邑之間的隙地。以往這些荒僻之地靠粗笨的石器農具不能耕作,如今有了鐵器工具和國家組織的大墾荒和水利道路建設,可耕面積便很易擴闊,城市人口也日漸增加,地處文明地區外圍的國家往往更易向蠻荒之地開拓疆土。能熬到最後的「七雄」都在開邊拓遠,最終成為贏家的秦國更樂此不疲。龐大的官僚管治新系統少不了「吏」,由飽學的食客到雞鳴狗盜之徒組成的「士」便是其後備。儒家能拔地而興, 是因為能給新世界培訓更多的「士」去充任「吏」。而諸子百家就是當時最出眾的「士」, 他們有如當下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指點江山,懷瑾握瑜,待價而沽。如今我們日夕侃侃而談的國族特性,有許多思想深層的基因都是在這轉折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