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求真的誠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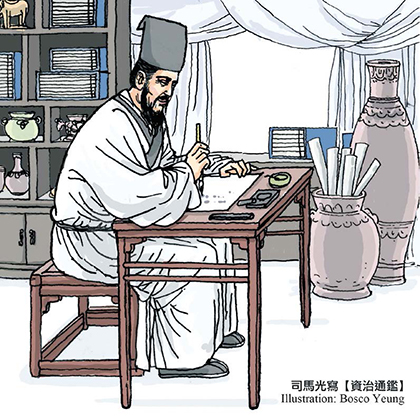
日本講談社近年還有另一套值得稱道的叢書叫《中國的歷史》,從古史上的傳說時代講到近代,共十卷,每卷由專注該時段的日本學者執筆。卷首都有內地在該領域最有聲望的學者的推介文章。簡體中文版是二○一四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製作,原版有十二卷,其中有兩卷不便在大陸發行,後出的台灣繁體中文版則有齊日文版的內容。
坊間通史常如流水漲,腔調則近乎歌劇裡黃門官的宣叙調,冠冕堂皇,理由欠奉, 令人想起舊時江湖賣藥佬的口頭禪:「你唔聽都得,唔信就唔得。」。有識者把這治史的方法稱為「歷史編篡學」,竊以為歷史之所以令芸芸學子一出校門便掩耳疾走,九成是這些悶絕人寰的書在「累街坊」。國人愛把國史稱為「一部廿四史」,這傳世的廿四套史書被目為正史,大致都為所寫該朝消亡後修編,某些史實牽扯到修史朝廷好惡,不免投鼠忌器,且一眾史家見解不同,矛盾是意料中事。司馬光把宋前的一千三百年史事重寫,取名《資治通鑑》,認定史書如寶鏡,陟罰臧否得當,為政者才能以古為鑑。正統史書當然全都以儒家史觀過濾和選材, 但何者才是儒家正統,人人譜尺不同。何況歷史說到底是回憶,任何人的回憶都有選擇性,幾乎可說,無非只乃樂於回憶的東西, 而歷代學者在這些回憶基礎上所作的再闡述則是再一層過濾和渲染,後人讀到的便難免是這些人人「借他人酒杯來澆自家塊壘」的層累,要真的貼近真相,談何容易?世上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有其屬意的歷史大敍述,有時走到極端,御用寫手說老祖宗的故事都有若文宣,只要有需要,捩橫折曲,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決不臉紅。成王敗寇,今古如一。但人類文明無論中西,學林定有不甘隨波逐流之人。在人間談真理講誠信也許很奢侈,但若公然否定人該追尋真理或真相, 人和禽獸還有何區別?王者又如何能堂而皇哉地享國?由是我們的史書雖不乏為尊者諱的「識做」傳統,但也必有「只問真不真, 不求用不用」的書呆子秉持正氣著書立說。「一部廿四史」讀來不乏孟子說的「浩然之氣」,只因還有這些人寫的這些書存世。
也許是旁觀者清吧,《中國的歷史》不但精準地理清了正統的學界共識,還收進了許多因近年考古發掘及以較新觀點爬疏舊說的新發現。讀來不免驚嘆,每隔三數十年, 每門學問都在天翻地覆,想不陷於淺陋,唯有多讀多學。手邊有本美國學者羅泰的大作《宗子維城》,便有意避開傳世文獻,光從考古材料的角度考察孔子時代的中國社會, 提出許多很有意思的猜測。恰巧剛讀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版「中國斷代史系列」中的《西周史》和《戰國史》,兩部都是○五年才過身的著名史家楊寬的力作。他和羅泰走的路線相反,主力還是立足於對正統文獻的解讀, 卻不一定遵從舊說,且還對許多讀舊書時不禁發生的疑惑窮追不捨,「臨門一腳」時常踢得「到喉到肺」,令人讀來常精神一振。可見著書者是否非我族類,立論和切入點是否正統並不是問題。書能否吸引人讀下去,求知的誠意才是關鍵。好書常令人有如進入一個到處都有刺激你求知慾亮點的大觀園,令人感到結論都是開放的,真相都是浮動的。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這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又何妨視所有成說和定見為猜測,窮究下去?書呆子人生的至樂,也許亦不外如是吧?(書的故事.10)





















